原名:The Fire of Mazda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译者:美亚
未经译者允许,禁止无端转载
前注:篇名中的马兹达指琐罗亚斯德教(别名马兹达教)崇奉的神主和造物主阿拉胡·马兹达
关于《马兹达之火》
About “The Fire of Mazda”
在上一个故事的事件之后,西蒙(Simon)¹并没有休息太久。《马兹达之火》中,公元27年的初秋,麻烦再一次找上了西蒙。这个故事初次发表于1984年5-6月《猎户座的孩子(Orion’s Child)》的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
[注1:西蒙·马古(Simon Magus),原型为《使徒行传》第八章中所提到的,在撒玛利亚“行邪术的西门(Simon the Sorcerer)”、“神的大能”。他是公元一世纪一个持诺斯替主义的撒玛利亚人,也是买卖圣职(Simony)的创始人,早期基督教认为西门是“异端之父”,诺斯替主义的先驱]
尽管蒂尔尼说过“这个故事的特色更多归功于E·R·艾丁生(E. R. Eddison)¹,而不是诺斯替主义”(Letter, June 1, 1984),但这真的是个诺斯替主义的故事。并且至少向琐罗亚斯德教,古伊朗的伟大二元论宗教致以同样多的敬意。琐罗亚斯德教经常被认为是诺斯替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特别是理查德·瑞真斯汀(Richard Reitzenstein)²的《希腊秘仪宗教:它们的基本思想与意义(Hellenistic Mystery Religions: Their Basic Ideas and Significance, Eng. trans.,1978)》,他为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直接联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论据,在巴比伦/波斯之囚(Babylonian/Persian Exile)期间,形成了犹太教末日论(Jewish Apocalyptic)与诺斯替主义,也见最近诺曼·科恩(Norman Cohn)³的《宇宙、混乱与未来的世界:末日论信仰的古老根源(Cosmos, Chaos and the World to Come: The Ancient Roots of Apocalyptic Faith, 1993)》。琐罗亚斯德教与三世纪摩尼教的灵知派具有尤其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二者都是光暗二元对立(dualisms of Light versus Darkness),协调善恶(coordinated with Good versus Evil)。
[注1:艾立克·洛克·艾丁生 (Eric Rücker Eddison)(1882年11月24日—1945年8月18日) 为英国公务员、作家。使用 "E.R. Eddison."的笔名创作]
[注2:理查德·奥古斯特·瑞真斯汀(Richard August Reitzenstein,1861年4月2日-1931年3月23日) ,一名德国古典文学家与学者,研究古希腊宗教、赫尔墨斯主义与诺斯替主义,被库尔特·鲁道夫(Kurt Rudolph)称作“最振奋人心的诺斯替学者之一。”]
[注3:诺曼·鲁弗斯·科林·科恩·英国国家学术院(Norman Rufus Colin Cohn FBA,1915年1月12 日-2007年7月31日),一名英国学者、历史学家和作家]
(与宗教)同名的马兹达是先知琐罗亚斯德(the Prophet Zoroaster, or Zarathustra, or Zardusht)心中最主要的神明。他通常被称作阿胡拉·马兹达,“智慧之主(Wise Lord)”或者“光之主(Lord of Light)”。因此,他似乎与吠陀(Vedic)神明伐楼那(Varuna)相同。琐罗亚斯德是一名伊朗的吠陀祭司,他拒绝了吠陀婆罗门教诸神,也就是提婆(devas)¹,将他们视作恶魔,恢复了智慧之主伐楼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保留了吠陀密特拉(Mitra)²与阿塔尔(Atar)³,即阿耆尼(Agni)各种各样的从属地位。
[注1:提婆(梵文:देव、英语:Deva),天的意思,印度教用来指居住在天界的男性神明,琐罗亚斯德教与之对应的则是迪弗(阿维斯塔语:Daēva、波斯语:Deyv),被认为是恶魔和阿赫里曼的走卒]
[注2:密特拉(原始印度-伊朗语主格形式为*mitrás,现代波斯语为میثره),一个古老的印度-伊朗神祇。这一神祇原是雅利安人万神殿里共有的崇拜对象,在伊朗-雅利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分化之后,开始向着不同特征发展
琐罗亚斯德教的密特拉是光明与誓约之神,他的名字前面常常冠有“领有辽阔原野的”这一固定修饰语,意思是说全世界的原野都在其视野范围之内,另外,“罪恶昭彰的阿赫里曼(波斯语:Ahrīman)在他面前不寒而栗(引自元文琪译本《阿维斯塔》,也是国内唯一译本)”]
[注3:Atar(阿维斯塔语:Athra、波斯语:Ātash/Ādhar、帕拉维语:Ātakhsh/Ātur/Ātar),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之神,他被尊为阿胡拉·马兹达之子,二者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父子关系,这是为了强调其作为火焰象征的神圣性,也可能是由于阿胡拉·马兹达本身的超然]
我们还发现故事中召唤了一个叫做阿兹达哈克(Azdahak)¹的恶魔存在。阿兹·达哈卡(Azi Dahaka)是古伊朗宗教中一条丑恶的邪龙,“他有三张嘴、三颗头、六只眼与一千种变化(perceptions),是个非常强大的恶魔骗子(liar)、世界上最邪恶的骗子、安哥拉·曼纽(Angra Mainyu),即阿赫里曼(Ahriman)²带来的最强大的骗子……为了摧毁真理(Truth)的世界(Aradwi Sura Anahita³ IX:4)”。这个强大的存在被允许统治世界一千年,之后英雄法里顿(Feridun)⁴把他绑在了一个深坑里。因此,阿兹达哈克与他的地狱主人,似乎是犹太教与《新约》将撒旦从上帝的仆人变成他头号敌人的主要灵感,特别是反映在《启示录》20:1-3里。回想起诺斯替主义将圣经里的雅威降格成自大的德缪歌(Demiurge)⁵,他把《妥拉(Torah)》⁶给了摩西。据说阿兹达哈克撰写了《托拉》,并建立了耶路撒冷城。最后,洛夫克拉夫特在《无名之城》里提到的《一千零一夜》里的角色,阿弗拉西亚布(Afrasiab)⁷与他那一船恶魔,构成了阿兹达哈克神话集(myth-cycle)的一部分。
[注1:Azdahak(阿维斯塔语:Azhidahāka、波斯语:Azhdahāk),琐罗亚斯德教恶神之首阿赫里曼为了破坏世界而创造出来的恶魔,三张嘴巴、三颗头、六只眼与上千种变化的邪龙,统治波斯千年的蛇王扎哈克(Zahhak),被视为邪恶宗教,包括犹太人的宗教的起源,也是魔法的开创者。在《扎姆亚德·亚什特(Zamyad-Yasti)》里,与阿胡拉·马兹达的造物阿塔尔抢夺阿胡拉·马兹达的凯扬灵光(Farr-e-Kayani),因此二人被视为宿敌,至于perceptions,大概是阿维斯塔语翻译问题,元文琪译本《阿维斯塔》使用了变化,所以我也采用了变化]
[注2:Angra Mainyu(阿维斯塔语:Angra-Mainyu、波斯语:Angra-Mainyu/Angra-Meynou),琐罗亚斯德教恶神之首,阿赫里曼的别名,是世界之初的恶本原,与斯潘德·曼纽对立]
[注3:Aradwi Sura Anahita(阿维斯塔语:Aredvī-Süra-Anāhīta),由三个词组成的复合词,意为“纯洁而强大的河流”。“阿娜希塔”在波斯文中称作“纳希德(Nāhīd)”,含有“金星”之意。她是江河的庇护神,被描绘成雍容华贵的妖娆女子(摘自元文琪译本《阿维斯塔》)
此处应该是对同名书籍的引用]
[注4:Feridun(波斯语:Farīdūn),常被称为“名门望族出身的法里顿”,传说中伊朗第一个王朝,丕什达德(阿维斯塔语:Paradhāta、波斯语:Pīshdādyān)王朝他曾献给阿娜希塔百匹马、千头牛与万只羊,祈求打败达哈卡,并得愿以偿]
[注5:Demiurge(字面意思是希腊语的工匠),物质世界的造物主,亦即诺斯替版的《旧约》之神,并非至高神。移涌(Aeon,字面意思是希腊语的永恒)是指从神那里流溢出来的东西,是围绕着神的的能量。最小的移涌索菲亚(Sophia,智慧的意思)想要独立孕育一个肖像(likeness),所以在不经过神与其阳性配偶同意的情况下,产出了盲目而不自知的德缪歌,因为是独立孕育,所以德缪歌与她并不相像,同时,索菲亚也因对不可见的光明/“父”的追求堕落,造就了低级索菲亚(lower Sophia),即本文提到的阿卡穆特(Achamoth),不过本文阿卡穆特其实更偏向于德缪歌]
[注6:Torah,妥拉广义上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义,亦指上帝启示人类教导与指引。狭义上指《旧约》的首五卷。]
[注7:Afrasiab(阿维斯塔语:Frangrasyan、波斯语:Afrāsīyāb),突朗(阿维斯塔语:Tūiriiānəm、中古波斯语:Tūrān)王朝的著名国君,曾三次下水追逐灵光未遂,是传说中伊朗第二个王朝,凯扬(阿维斯塔语:Kaviyān、波斯语:Kaiyān)王朝诸国君的宿敌,后被其中一任国君,凯·霍斯鲁(阿维斯塔语:Kavi-Haosravah、波斯语:Kay-Khosrau)抓获并处死,为父报仇]
正文:
I
A lovely lady garmented in light
一个可爱的淑女,她的躯体
From her own beauty—deep her eyes, as are
沐浴于美的光华——她目光深沉,
Two openings of unfathomable night
犹如透过庙宇屋顶的缝隙
Seen through a Temple’s cloven roof—her hair
看到的深邃夜空中两个幽洞——
Dark—the dim brain whirls dizzy with delight,
她乌发披肩——看到她,一阵狂喜
Picturing her form; her soft smiles shone afar,
令人晕眩;她的微笑多迷人,
And her low voice was heard like love, and drew
她轻柔的声音似在诉说着爱情,
All living things towards this wonder new.
吸引着一切生命向她靠近。
— Shelley, “The Witch of Atlas”
——雪莱《阿特拉斯的巫女》¹
[注1:引自顾子欣译本《雪莱全集》]
“魔法,”多西修斯(Dositheus)¹说,“不过是世界心灵(the Mind of the World)引导自身意象(images)改变的方式。每一个拥有真灵(True Spirit)²的人,都是伟大世界心灵(World-Mind)的一部分。因此……”
[注1:Dositheus/Dositheos,有时也被称为纳撒内尔(Nathanael),意思都是“上帝的礼物(gift of God)”,是个阿拉伯血统的撒玛利亚宗教领袖。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带有诺斯替性质的撒玛利亚教派的创始人,被认为认识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并且要么是西门·马古(Simon Magus)的老师,要么是他的对手(译自Wikipedia)]
[注2:True Spirit,诺斯替主义将人分为肉(Flesh)、魂(Soul)、灵(Spirit)三部分,德缪歌因渴求异乡神(The Alien God)遗失于物质世界的灵,与六个阿其翁(Archons)一起创造了魂,作为外衣包裹着灵,又以肉体包裹魂,使人的灵性被蒙蔽,永远沉沦于物质世界,但蒂尔尼似乎没有特意区分魂和灵,事实上诺斯替一些经文也只是特定时刻会去区分,所以除了True Spirit,我会全部翻译成灵魂,不过会将相关词汇的原文标注出来]
“停下!”西蒙尖叫着站起来。他颤抖着站在那里,一只手捂着眼睛,另一只手伸开,好像要抓住什么无形之物。
宣讲者是个穿着撒玛利亚巫师袍的瘦弱男人,他带着担忧的神情,向前弯着腰。虽有火把的微光,但仍然昏暗的房间里,另外两人也是如此。一个矮胖的秃顶男人穿着罗马贵族的服装,还有一个大约11岁的少年,少年穿着和宣讲者同款、饰有符号的棕色长袍,右肩上蹲着一只乌黑的大渡鸦。
“那是什么?”多西修斯问道。“说吧,西蒙。我的话有没有让你想起什么?”
那个叫西蒙的男人静静的站了一会儿,他的颤抖消失了。他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年轻人,脸上棱角分明的颧骨显得与众不同,但似乎与说话者和那个十一岁的少年是相似人种。他身着一件黑色的无袖束腰外衣(tunic),脚上穿着高带凉鞋(high-strapped sandals)¹。在他的腰上挂着一把西卡(sica),或者说是一把弯曲的角斗士短剑。
[注1:high-strapped sandals,罗马人常穿那种凉鞋(如下图),我实在不知道中文一般叫它什么,问了一圈人也没得到答案,暂时这样翻译了]
“你的话……”他低声道,听起来格外紧张。“它们唤起了一种意象(image)——一种异象(vision)¹……”
[注1:vision,诺斯替主义认为异象不是通过魂,也不是由灵看到的,而是用二者之间的心灵(古希腊语:νοῦς、英语:Mind)看见的,不过本文明显没有区分,所以只在专有名词以及异象相关时特意翻译成心灵]
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肩上的渡鸦不安地拍打着翅膀;矮胖的罗马人弯了弯腰,嘴张得大大的;多西修斯挺直了身子,一脸严肃。
“异象?告诉我吧,西蒙。”
“我看见了一个女人。”西蒙心不在焉地拂去了他宽额头上的黑色刘海,它们立刻落回了原位。“一个头发和眼睛漆黑如夜的年轻女人,星星在她的头发和眼睛中闪烁,就像在夜里一样……”
他沉默了,弯下腰来,若有所思地盯着自己的手背。
行邪术的(sorcerer)¹老撒玛利亚人多西修斯站了起来,露出微笑。“你看到了真的异象,吉塔的西蒙(Simon of Gitta),”他平静地说。“我很少见到这样的异象,正如我所怀疑的,你绝对是个真灵。”西蒙没有回答,他抬起头,凝视着前方,仿佛要捕捉一个正在消失的画面,然后他带着失望的表情,转向了多西修斯。
[注1:sorcerer,虽然读起来可能有点拗口、中二,但考虑到西蒙的原型就是“行邪术的西门”,所以本文里诸如sorcerer、sorcery、sorcerous之类的都译成邪术了,实际上就是魔法]
“告诉我,我的导师——她是谁?”
多西修斯平静地看着西蒙,但他的眼里有一种悲伤。“她是祭品,西蒙——你必须杀死她。我告诉过你,这异象必然降临到你身上,现在果然应验了。”
西蒙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太美了……”他喃喃地说。
“不!”多西修斯挺直了身子,他黑色长袍上的占星术符号看起来几乎要发光了,布满皱纹的脸严肃得像个古老的先知一样。“别这么想。坚定你的意志与心灵,西蒙,她的死会使我们向罗马复仇——我们一直渴望的复仇。”
西蒙使劲摇了摇头,像是要理清思路,然后站了起来,就像潜水员从水中浮出,进入新鲜的空气一样。“你说什么?多西修斯,你说的,就好像这个女人——我看到的异象——真的存在一样。”
“她。”多西修斯的眼中再次闪过一抹悲伤。“她在这里,就在我们的庇护人,朱尼厄斯议员(Senator Junius)的这所房子里。”他朝着那个矮胖的秃顶罗马人点头。“现在……”
西蒙阴沉地皱起了眉头。“你说她是——是我必须杀死的那个人?”
“是啊!”多西修斯大叫道,他的眼中突然闪烁着一种黑暗的狂热。“你应该杀了她,西蒙,你和我们一样憎恨罗马。罗马人不是因为你父母不能纳税,就在他们撒玛利亚的家里杀了他们吗?罗马不是把你变成了一个奴隶、一个角斗士,为了取悦她而浴血奋战,直到两年后,我和我的庇护人朱尼厄斯终于把你释放了吗?”西蒙怒视着地板,紧握在身体两侧的双手颤抖着。
“你还记得!”多西修斯继续说,他的声音很激烈。“你将复仇——你,还有我们所有人。向罗马复仇!听着,西蒙!”行邪术的撒玛利亚人向前弯腰,眼睛炯炯有神。“罗马是整个物质世界中最大的恶。你经历过那种邪恶,却不知道它从何而来。现在我来告诉你。”
“魔法,正如我所说的,是世界心灵(World-Mind)改变自己的方式,每一个真灵都是那心灵(Mind)的碎片,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碎片,西蒙。好好想想吧——这意味着你是终极之神(the Ultimate God)破碎灵魂(the sundered soul)的一部分。”
“你在胡说什么?”西蒙问道。“如果我是神之心灵(God-Mind)的一部分,那为什么我没有力量……?”
多西修斯举起一只手。“终极之神(The Ultimate God)是超越物质的,但很久以前,他落入了邪恶造物主(the evil demiurge)阿卡穆特的力量之中,古波斯人称之为阿兹达哈克,斯泰吉亚人(Stygians)¹称之为阿撒托斯。就这样,那位神在许多血肉之躯(fleshly bodies)中经受痛苦和限制……所以,我们都在这里。”
[注1:斯泰吉亚(Stygia)是罗伯特·E·霍华德 “柯南”系列里的一个国家]
“现在,罗马是阿卡穆特最新、最惊世骇俗的体现,但在灵魂(spiritual)层面上,他也统率着原初神(the Primal Gods)¹,他们的爪牙(minions)渗透了宇宙中的所有物质,意图引起一切可能的痛苦。这种痛苦上升到星体(stars)²,作为灵魂能量(spiritual energy)滋养原初神,以及终极的阿卡穆特本身。”
[注1:the Primal Gods,应该是primal god的变体,一个诺斯替主义概念,对于约翰启示录派来说,就相当于其他派别的“父”,而之上的太一(Monad),则是在自身的沉默与静止(silence and stillness)中超越一切,不可知(unrecognizable)的“先父(Pre-Father)”]
[注2:stars,诺斯替的世界观中,宇宙的各个层面就像围绕着地球重重排列的不同壳层,一般共有八层或者九层,德缪歌掌管恒星层,诸多阿其翁掌管行星层,恒星层之上则是神的国度]
西蒙反思了多西修斯的话。他想起了一生中经历和目睹过的所有可怕且不必要的痛苦,他的父母被罗马税务官杀害——他被残忍地奴役,训练成角斗士……最近,他曾战斗过的角斗场被邪术破坏,随之而来的是成千上万观众的死亡……
当然,多西修斯关于可怖神明的言论肯定只是虚假的疯狂幻想。西蒙想知道,为什么撒玛利亚巫师费了这么大劲来救他,却只是把他藏在朱尼厄斯议员的地窖里几个月?
“我曾告诉过你,西蒙,”多西修斯说,仿佛读懂了他的心思,“我感觉到你是一个天命之人(man of destiny)。我的占卜已经证实了这点。你不仅是一个真灵,而且是崇高者(the High Ones)之一——被阿卡穆特分裂并囚禁在他创造的物质世界的那位神最伟大的灵魂碎片之一。西蒙,你满脸怀疑,但是听我说:你的确是那位神的化身。现在你感觉到你的对应者,他者(the Other)的存在——是因为昨天,一个承载着她伟大灵魂碎片之一的少女被带进了这所房子里。”
“你疯了吗?”西蒙怒视着多西修斯,喃喃地说。
“我找了她很久了,”巫师平静地继续说,“通过咒语和占卜,以及我们的庇护人,朱尼厄斯议员雇佣的暗探。”他又朝那个矮胖的罗马人点了点头,罗马人正坐在酒桶上,满脸严肃。
“也花了很多钱。”朱尼厄斯说:“但最终我们找到了她——在以弗所的的伊奥尼亚城(the Ionian city of Ephesus)。她是个女奴和她贵族主人的女儿。她的名字是海伦(Helen),现在住在我家楼上。多西修斯告诉我,把她掳走(steal)是件相当困难的差事,因为她的父亲开始对她怀有非分之想,并且不愿接受任何价钱。幸运的是,我们雇佣的绑架者在他得手前就成功了,因为多西修斯告诉我,只有处女才能完成我们必须的牺牲(sacrifice)¹。”
[注1:sacrifice,与下文的献祭是同一个词,但这里有种伟大事业所必须的牺牲的感觉,加上多西修斯也将西蒙在角斗场杀人描述为sacrifice,感觉献祭不太符合语境,应当是双关]
“牺牲?”西蒙正对着罗马议员,出于某种原因,他的拳头紧紧攥在身体两侧,以至于胳膊都在颤抖。接着他感到多西修斯的瘦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西蒙,现在是时候让我指导你履行义务了。朱尼厄斯议员,你能允许我和我的学生单独谈谈吗?”
“明白。”罗马人站了起来。“好好指导他,让他为解放罗马于水火之中尽一份力。多西修斯,我为你的邪术知识花了很多钱,你表现得很好。只要再努力一点点,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残酷的暴君被推翻,共和国(Republic)就会重建。”他转身登上了通向地窖的石阶。
“我和卡波(Carbo)可以留下吗?”肩上停有一只渡鸦的少年说道。
多西修斯点了点头。“好的,米南德(Menander)¹。它会促进你学徒生涯的发展。跟我来——还有你,西蒙。”
[注1:Menander(希腊语:Μένανδρος),是公元一世纪撒玛利亚的一个诺斯替主义者和魔法师。他属于西门派(the Simonians),在他的导师和指导者西门·马古去世后,成为了该派的领袖]
他从支架上拿起火把,领着他们进入地下室更深的房间。这是个空无一人的小房间,只有中间有一大块立方体的石头,后面是一尊浅灰色的石雕。
“西蒙,你将在这坛上献祭。”西蒙凝视着这尊雕像,它的高度略低于四英尺,在本质上似乎完全呈现出守旧——一个穿着托加长袍(toga-clad)¹,高举一只手,头发上戴着月桂花环的罗马人。
[注1:一段呈半圆形长约6米,最宽处约有1.8 米的羊毛制兼具披肩、饰带、围裙作用的服装(如下图)。穿着时一般在内穿一件麻制的丘尼卡。]
“那里只有一尊皇帝提比略的雕像(an image of Tiberius, the Emperor)¹,”他咆哮着。“你让我对他献祭……?”
[注1:提比略,全名提比略·恺撒·(奥古斯都之子·)奥古斯都(拉丁语:Tiberius Caesar Divi Augusti filius Augustus,公元前42年11月16日-公元37年3月16日),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第二位皇帝,公元14年9月18日-公元37年3月16日在位]
“安静点,西蒙。不是对他,而是针对他(Not to him, but against him)。当你完成仪式,将你的色雷斯匕首刺入祭品的心脏,被激怒的诸神将会苏醒(stir),用闪电杀死提比略,一如往昔他们杀死赫斯提利乌斯王(King Hostilius)¹。然后,在朱尼厄斯议员和许多其他人的拥护下,塞扬努斯(Sejanus)²将掌权,并恢复旧的共和制度(Republican order)。暴君的统治将会终结。”
[注1:图鲁斯·赫斯提利乌斯(Tullus Hostilius,公元前672年-公元前640年),传说中的罗马第三任国王。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所说,与他的前任不同,图鲁斯被认为是个好战的国王,他认为前任更倾向于和平的性质削弱了罗马。据证实,他渴望战争,甚至比罗马第一位国王罗慕路斯(Romulus)更好战。关于图鲁斯·赫斯提利乌斯之死的记述各不相同。在李维记述的神话版本里,他激怒了朱庇特,然后朱庇特用一道闪电杀死了他。另一方面,非神话的原始资料描述了他在32年的统治下死于瘟疫]
[注2:塞扬努斯(英语:Sejanus, Lucius Aelius),(前20年-31年)。提比略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官员之一。公元14年至31年先后担任近卫军司令及执政官等职位。后因为被人告发其企图夺权篡位,被提比略处死(摘自百度百科)]
西蒙一提到塞扬努斯就发作了,他被认为是提比略完全信任的人,也是罗马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现在他知道朱尼厄斯哪来的钱去资助他昂贵的事业了。
“你是在豪赌。”西蒙说。“你怎么让这些强大的罗马人相信你的魔法不会欺骗他们?”
“它骗了你吗,西蒙?我曾前往帕提亚带回了斯巴达克斯(Spartacus)¹的剑,它让你有机会杀死罗马最强大的角斗士。这么做释放了魔法,摧毁了菲迪尼(Fidenae)的大竞技场,杀死了将近五万热血沸腾的罗马观众。那是你第一次牺牲,西蒙,它给所有憎恨罗马及其压迫的人带来了欢乐。现在到了你第二次牺牲的时候了,它的成果将更大,因为它将推翻这个罗马政府本身,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都将从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注1:斯巴达克斯(希腊语:Σπάρτακος、拉丁语:Spartacus),?-约公元前69年。是一名古罗马色雷斯角斗士,军事家,于公元前73年与高卢人克雷斯、埃诺玛依以及甘尼克斯一起领导了反抗罗马共和国统治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摘自百度百科)]
“权力的仪式,”西蒙嘟囔着。“我一拳就能把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国家从罗马手中解放出来?甚至,为了做到这点,我必须把我的剑刺入一个无辜少女的胸膛……听着,多西修斯,你怎么会懂这种事?”
“我走了很远,”撒玛利亚巫师说,“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从帕提亚带回了斯巴达克斯的剑,你可以用它重创罗马。但那把剑不是我唯一带回来的东西。看——”他指了指灰色的提比略雕像,“这雕像是我从扎瓦隆山(the mountain of Zavalon)上凿下来的,琐罗亚斯德曾居住在那里,他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善恶相争舞台的伟大先知。琐罗亚斯德一生都在与邪恶斗争,最后他被邪恶者(the Evil One)阿兹达哈克的人类仆从(servitors)们用剑击败。然而,光之主马兹达还活着——而你,吉塔的西蒙,是他最新的碎片化身和骑士(His latest fragmentary incarnation and champion),你很快就会为他而战。”
西蒙头晕目眩。他环视了一下地窖,注意到了墙壁和地板上潮湿的石头、酒桶和双耳罐、蜘蛛网,以及被多西修斯手中火把照亮的木梁——任何能帮他内心与物质且平凡的现实保持联系的东西。
突然,他转向多西修斯。“你疯了!”他咆哮道。
然后他转身跑出房间,穿过地窖,走上台阶,来到朱尼厄斯议员名下的露天花园,享受那让人头脑清晰的阳光。
西蒙匆匆走出花园,进入狭窄的鹅卵石街道时,没有一个人会拦下他,因为他以前就常被允许去买点东西或者散步锻炼。
他快步向前走了几分钟,直到他突然想起自己没有乔装打扮。
他停下身来,用一只手揉搓了几下刮过的脸。自从他到了朱尼厄斯家,这是他第一次不戴隐藏身份的假胡子(an artificial beard and mustache)——更别说连帽斗篷了……
他耸了耸肩,继续上路。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在菲迪尼的角斗场战斗了——那个角斗场的倒塌害死了大部分观众,足有上万人¹。他不用担心会被发现,因为那不大可能。再者说,他现在还要考虑其他事。
[注1:the arena that had collapsed, killing most of the thousands of spectators,从西蒙的耸耸肩,不担心被发现来看,他已经释怀了,但我想了几种译文,要么不通顺,要么读起来有种西蒙在忏悔的感觉……]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沿着西莲山(Caelian Hill)¹的东北坡,穿过了羊肠小道。这是个混合区域,朱尼厄斯议员的官邸也只是这片区域恢宏气派的宅第之一,但还是有许多中下层民众住在这里。罗马,正如西蒙已经注意到的,是穷奢极侈、一贫如洗以及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体,似乎各种元素都没有尝试把自己切割(separate)²出去。
[注1:Caelian Hill,罗马七丘之一,后文也会出现其他几座山丘。古罗马七丘位于罗马心脏地带台伯河东侧。根据罗马神话,其为罗马建城之初的重要宗教与政治中心,当时的七座山分别为凯马路斯(Cermalus)、契斯庇乌斯(Cispius)、法古塔尔(Fagutal)、奥庇乌斯(Oppius)、帕拉蒂尼(Palatium)、苏古沙(Sucusa)与威利亚(Velia);而传说中罗马城最初是由罗慕路斯(Romulus)于帕拉蒂尼山(Collis Palatinus)上兴建。(Collis Aventinus)、卡匹托尔山(Capitolinus)、奎里尔诺山(Quirinalis)、维弥纳山(Viminalis)、埃斯奎里山(Esquilinus)与西莲山(Caelius)(摘自百度百科)]
[注2:separate,这个词既有切割的意思,又有与某(群)人分离/断绝关系的意思,而现在网上也会用切割表示后者,所以就这样译了]
他走近山脚和居民区的边缘,然后拐进了狭窄的墨丘利街(Mercury Street),继续往前走。小贩和乞丐沙哑的嗓音向他袭来,傍晚的温暖中,汗水、粪便、腐烂的水果和肉类的臭气像块湿布一样,笼罩在他的脸上。墨丘利街!他们怎么敢用神的名字来命名这条小巷,而不畏惧自己亵渎的罪行会招来死亡……?
他向左转,上了苏布拉(Subura)一条更宽阔的大道,然后匆匆前行,最后他出现在一个不那么让人不适的地段,一片被庄严的圆柱神庙和政府大楼包围的空地上——广场(Forum)富丽堂皇的地区。和往常一样,西蒙停下来惊叹。无论他多少次看到这些闪闪发光的墙壁和柱子,他都无不感到敬畏;无论他有多恨罗马,他都不能否认她确实是世界的掌权者。
他继续往前走,瞥见了他左边的神庙之间,帕拉蒂尼(Palatine)——罗马贵族圣地的斜坡上的豪宅和宫殿的白色门廊,它们像熠熠生辉的珍珠镶嵌在周围的青枝绿叶中。他面前矗立着最宏伟的建筑——罗马最强大的神,朱庇特(Jupiter)富丽堂皇的圆柱神庙,若隐若现地高耸于卡匹托尔山(Capitoline Hill)的山顶之上。
“罗马!”西蒙轻声抱怨,说完就感到了一阵仇恨。
他仍然继续往前走,沿着蜿蜒的小路,踏过无数的石阶,一直走到卡匹托尔山的山顶,最后他站在直通朱庇特神庙柱廊的宽阔台阶上。罗马在他脚底下展开,潮湿的空气和无数的炊烟混合,令罗马变得模糊。西边,就在贾尼科洛(Janiculum)南脊的上方,太阳正在落下,变成了无光的红火球;东边,大量的云团正向前飘着——棉花似的冷光巨浪矗立着——在它们之下,阿尔巴山(Alban Hills)消失在深深的阴影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即将下雨的感觉。
西蒙爬上了阶梯,随即却不想进入这有着邪神崇拜般的神庙,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¹,他向左拐,沿着圆柱门廊的边缘走,一直走到尽头。他的脚下是塔平(Tarpein)悬崖,不计其数的罪犯,或者说是罗马的敌人曾被扔下去。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感觉到那向下的深渊就像黑暗的真空一样拽着他。云似乎在这无声的庄严中前行,渐渐变暗;下面,一队人正沿着小路迂回前行——一小群礼拜者带着一头白色阉牛去祭祀卡匹托尔的朱庇特(Capitoline Jupiter)……
[注1:Simon climbed the stair, but then, feeling a reluctance to enter what he felt was a fane of idolatry,个人感觉以西蒙对于罗马的情感,他大概会觉得朱庇特是个邪神,加上说偶像,现在的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指某些明星,所以就译成邪神崇拜了,而原文也只是西蒙觉得朱庇特是邪神,并不一定,所以稍加改动]
接着,西蒙似乎突然在黑暗的云层里看到了一张脸——仅仅是在一个小时前,在朱尼厄斯议员那燃着火把,微光点点的昏暗地窖里,他心灵中看到的那张脸。
“巴力啊(Baal)¹!”他倒吸一口凉气。“什么……?”
[注1:巴力巴拉,是古代西亚西北闪米特语通行地区的一个封号,表示“主人”的意思,一般用于神祇。这个封号源自于迦南人的神明,是希伯来圣经中所提到的腓尼基人的首要神明,曾被用于不同的偶像]
那是张女人的脸,参天又硕大,似乎俯瞰着他,俯瞰着整个世界。同时,她又是娇贵、短暂、脆弱的,或者说是某种能滋润万物,却又昙花一现的东西。不知怎么的,他知道他看见的只是云,没有别的东西,在这伟大的罗马城里,没有人能看见他看见的东西——当然,他也知道他看见的是伟大的真实(a great Reality),而罗马只不过是一场梦幻泡影。
“我认识你,”西蒙喃喃道。
我也认识你。¹
[注1:原文为斜体,为了方便阅读,改成加粗了]
心灵中的意念之声十分洪亮,像遥远的雷鸣,但又很柔和,就像亲人在芬芳馥郁的黑暗中的低语。太阳西沉,乌云也越来越暗。它们翻腾的褶皱就像一绺绺卷发,在逐渐变暗的烛光下闪烁;它们的高光就像一位美丽女神乳白色的五官;而两处阴影区域,则像是从宇宙尽头闪烁而来的星潭:那倒映着明眸的黑暗深潭……
“我认识你!”西蒙突然大吼着伸出双手,就像他是一个祈祷者。“我见过你,但是在一个小时前,在我的心灵里——在朱尼厄斯家的地窖里……”
尽管这么说,他还是感到自己很愚蠢。这些话在空气中刺耳地回荡着——太真实了,太实在了(too real, too physical)——当然,云也不过只是云,消散着,变幻着……
然后,他似乎又听见了那个声音,比之前更清楚了:
我认识你,吉塔的西蒙,从太古之时(aeons)我就认识你。你忘记了我,我也忘了你,然而我们从未真正忘记彼此。移涌们(The Aeons)只是把我们囚禁在时间与物质之中,但是没有我们,时间和物质将不复存在。我是赫拉(Hera),而你是朱庇特——是的,甚至和这些罗马人在这座黑暗的山上信奉的一样。我是自泡沫诞生的阿佛罗狄忒(Aphrodite),而你是赫尔墨斯(Hermes),那个曾接纳并征服了我,让我着魔的魔法之神(that god of Magic)¹。过去我是海伦(Helen)²,而你是特洛伊城(the walls of Troy)被攻陷时,那个占有我、爱着我(held and loved)的人。自从世界诞生以来,我们就常常相爱,又常常被迫分离,现在我们又走到一起了。听我说,吉塔的西蒙……
[注1:that god of Magic who once embraced and conquered me with your spells,阿佛罗狄忒和阿瑞斯被赫菲斯托斯捉奸在床,捆起来示众时,“宙斯王对赫尔墨斯这样说:‘赫尔墨斯,宙斯之子,引路神,施惠神,纵然身陷这牢固的罗网,你是否也愿意与黄金的阿佛罗狄忒同床,睡在她身边?’弑阿尔戈斯的引路神当时这样回答说:‘尊敬的射王阿波罗,我当然愿意能这样。纵然有三倍如此牢固的罗网缚我,你们全体男神和女神俱注目观望,我也愿睡在黄金的阿佛罗狄忒的身边。’他这样说,不死的天神们哄笑不止(引自王焕生译本《奥德赛》)。”事后阿佛罗狄忒为赫尔墨斯诞下了赫马佛洛狄忒斯,我不确定蒂尔尼是不是双关,认为赫尔墨斯用了什么魔咒,所以翻译成着魔了]
[注2:海伦(古希腊语:Ἑλένη、英语:Helen),宙斯与勒达之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本文中此时被抓进朱尼厄斯家的海伦,原型应为西门曾从腓尼基的提尔城(Tyre)带回来的妓女海伦娜(Helena),西门宣称自己是超越一切的“父”,海伦是一个名为Ennoea(意念的意思)的移涌,她也被称为普鲁尼可(Prunikos)与圣灵,西门通过她创造了众天使,然后天使们创造了世界与人类,出于嫉妒,将意念囚禁在了物质世界,永远在女性体内轮转,由于天使们都想得到她,所以她流落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战争,其中一世就是特洛伊的海伦,她的被救与世界的被救是不可分的,而“父”以西门的形式降临,就是为了拯救海伦娜]
云向前飘着,在沸腾中失去了形状。起风了,西蒙绝望地喊道:
“我该怎么办?告诉我!告诉我!”
你必须真诚,西蒙——真诚地对我,也真诚地做你自己……
乌云滚滚压顶,电闪之后,大雨滂沱。远处传来雷鸣。西蒙大吼起来,他绝望地寻找着一个名字,而他的舌头找到了。
“海伦!”他喊道。“海伦!”
暴风雨来了,西蒙从捧起的双手中抬起脸,意识到了他一直在哭。一层面纱被简单地揭开,披露出了不可思议的前景——关于力量和娱乐、憧憬和爱的宇宙记忆……
“海伦!”
西蒙再次用双手捧起脸,踉踉跄跄地走下了神庙的台阶。雷声轰鸣,大雨如注。西蒙对着耀眼的天空挥舞双拳,步履蹒跚地匆匆前行,他经常在泥里滑倒,一边咒骂着众神,一边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
II
Lo! in yon brilliant window-niche
瞧!在那明亮的壁龛窗里
How statue-like I see thee stand,
我看你玉立多像尊雕塑,
The agate lamp within thy hand!
那镶嵌玛瑙的明灯在手!
Ah, Psyche, from the regions which
啊,普叙赫¹,你来自圣地,
Are Holy-Land!
那天国净土!
— Poe, “To Helen”
——坡《致海伦》²
[注1:普叙赫(希腊语:Ψυχή、英语:Psyche),希腊神话中人的灵魂的体现,远古的时候被想象成人死后离人而去的鸟。从公元前5至4世纪开始,她往往被描绘成蝴蝶或长着蝴蝶翅膀的少女的形象(摘自百度百科)]
[注2:引自曹明伦译本《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
他发现自己靠在一堵砖墙上,上气不接下气,只是模糊地记得自己跑过了许多条街巷。显然,这场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雨已经停了,天空也有点放晴。他的头发和无袖束腰外衣湿透了,凉鞋和腿上溅满了泥。他四下观望,发现自己又一次来到了狭窄的墨丘利街。
“赫尔墨斯,魔法之神(Hermes, God of Magic),”他喃喃自语道,“救救我,让我逃离疯狂!多西修斯在我身上施了什么魔咒?他要让我参加什么邪恶的仪式?那个——那个女人现在真的住在朱尼厄斯议员的家里吗?我必须要确认一下!”
现在他已经恢复了呼吸——尽管最近几周很少活动,但作为角斗士的训练还是给了西蒙极佳的体力储备。他继续快步前行,穿过混乱而又狭窄的街巷,由于最近下了一场大雨,相对而言,这些街巷空荡荡的。最后,他在匆忙中慢跑,爬上了通往西莲山居民区的小道。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但是天空已然放晴,有充足的光线让他能看清前方的道路……
“停下!站住,别动!”
西蒙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见三个男人正向他逼近。他们拿着铁尖长棍,腰间佩戴着剑。看着他们设计奢华的斗篷和无袖束腰外衣,西蒙猜测他们不是城市巡逻队(the City Patrol)的常规军人,而是一些富裕的市民经常雇佣来,在他们附近的居住区巡逻的雇佣兵。
“你们想干什么?”他质问道。
“别对我们这么无礼,”其中一个人怒吼着。“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在街上跑来跑去,腰上还戴着一把剑。你抢劫了什么人,还是说你是个逃跑的奴隶?”
西蒙生气地皱起了眉头。“我既不是强盗(thief),也不是奴隶。”
“你能证明吗?”
西蒙把手伸进腰带上的小袋子里,抽出一张羊皮纸,递给了他。卫兵接过并展开了羊皮纸,仔细地眯着眼看了字迹。“上面说了什么?”他怀疑地问。
“这是我前任主人朱尼厄斯议员的释放令。我是他的自由民。”
卫兵把羊皮纸还给了它。“你说的或许是真的,”他说,现在他的语气不那么充满火药味了,“但还是要确认一下。跟我们来。我们庇护人的诵经员会检查你的令状,并告诉我们它是否有效。”
“我——我有急事,”西蒙说着,把羊皮纸塞回了他的小袋子。
“所以?你勾起了我的疑心!”卫兵向他的两个同伴挥手示意。“围住那只狗!我们要‘教’他讲些礼貌,然后我们……”
“帕拉斯在上(By Pallas)¹!”其中一人突然惊呼一声,与此同时,他移动到了一个能更清楚地看到西蒙的脸的位置。“是他——菲迪尼角斗场被邪术毁灭时战斗的那个角斗士!当时我在场——好不容易才逃过一劫……!”
[注1:Pallas,希腊神话中有许多帕拉斯,比如克利俄斯与欧律比亚之子,乌拉诺斯与盖亚之子,雅典娜的别名等,不确定指的是哪个]
西蒙咆哮着打了起来,拳头狠狠地打在了离他最近的卫兵脸上,卫兵一声不吭地败倒在鹅卵石上。他像豹子一样快速蹲伏下去,侧身一转,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开了第二个卫兵棍子的致命一击,转身之后,削铁如泥的(sharp-bladed)西卡已经在西蒙手里了,他划过卫兵的脖子,那个人在垂死的咯咯声中倒下了。
剩下那个卫兵转身跑掉了,他丢下了棍子,在惊恐之中发出尖叫,卫兵迈着荒唐可笑的大步,踉跄着下了鹅卵石山路。西蒙咒骂着。街上有人,他追不上那个人。他迅速地把色雷斯匕首插入鞘中,在这羊肠小道上匆匆前行,希望渐浓暮色的阴影足以掩护他逃离追捕。
“他逃走了!”朱尼厄斯生气地说,多西修斯站在议员家的柱廊边。“我的一些奴隶看见他跑掉了。”
“他没有逃跑,”多西修斯心平气和地向他保证,“有时间静下心来之后,他马上就会回来。除了对我们感激的绳结,他还被我们准备举行的仪式的咒语束缚着。”
年轻的少年米南德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徘徊着,他听着,脸上流露出不安,怀疑中混杂着好奇。渡鸦仍然栖息在他的肩膀上,似乎也在倾听,它那锐利的目光是多么专注。
“仪式。”朱尼厄斯慢慢摇头。“这么多仪式——现在,你说最后一个必须举行。我知道你可以召唤强大的力量,多西修斯,全罗马都在谈论菲迪尼竞技场的毁灭,我也已经听说过了。然而,有些时候我怀疑你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的疑惑何在,好朱尼厄斯?”
罗马人低眉深思。“那个女孩——你说必须牺牲的那个。她没有伤害任何人。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是啊,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沉重的事。但是,朱尼厄斯,你要记住,提比略和他的执法官们(agents)每天杀害无数无辜的人,他的军团压迫了所有地区和国家。在你看来,我们将要在众神面前做的这件事可能是令人憎恶的。好吧,它是——它将唤起众神的打击!当祭品被献给提比略的雕像时,阿卡穆特天球之上被冒犯的力天使们(the offended Powers above the Sphere of Achamoth)¹将发出愤怒的闪电炸死皇帝,无论他在哪里。”
[注1:Powers首字母大写了,所以可能指的是能天使,考虑到能天使也会被用来指代德天使(Virtues),所以译为力天使]
“让他们瞄准点!”朱尼厄斯怒吼道。“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我不用参加仪式。老实告诉我,多西修斯——会有危险吗?”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不会。不过,仪式期间,你和家人最好躲到地窖里,准备好在必要时从秘密通道逃走。”
“真的吗?”多西修斯用一只粗壮的手紧张地揉搓着他那肥下巴。“全都告诉我,巫师。什么都不要隐瞒。”
“发生危险的可能性非常小。星象是对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准备仪式都举行得无可挑剔。然而,如果祭品本身出了问题,力天使们或许会进行干涉。然后阿塔尔,伟大马兹达的火焰仆人(the fire-minion of Great Mazda)就会苏醒,从四维的瓦雷纳(Varena)¹出来,率领着他的烈焰军团,寻找我们仪式的源头,以杀死他的敌人,不洁者阿兹达哈克(Azdahak the Corrupt)被束缚在世界上的(earth-bound)追随者。无论如何,古代波斯的点火僧(fire-priest),奥斯当斯(Ostanes)²是这么写的……”
[注1:Varena,是扎哈克的出生地,瓦雷纳有诸多伪信者,即迪弗教徒,法里顿也正是在瓦雷纳献祭阿娜希塔的]
[注2:Ostanes/Hostanes/Osthanes(希腊语:Ὀστάνης),虚构的以炼金术闻名的巫师,被认为足以与发明占星术的琐罗亚斯德和以预言著称的海斯塔斯佩斯齐名,他被誉为“最伟大的麻葛(Magi,点火僧的一种,单数为Magus)”、“七弦琴之王(The Sovereign Of The Seven Sounds)”]
“够了!”朱尼厄斯喃喃道。“尽管你说的很离奇,但我也不怀疑你,因为我了解得够多了。我会遵从你的指示。”
“很好。现在,派几个最强壮的奴隶去地窖里,让他们去把石坛和石雕搬来,立在水池边柱廊的这里。日落将至,我必须在马兹达火热象征被地平线掩盖时,举行最后的准备仪式。米南德,如果你们愿意,你和卡波可以协助我……”
多西修斯转身面向少年,却发现他年轻的学徒已经不见了。他和渡鸦悄无声息地从柱廊溜走了。
米南德在大理石楼梯的顶端踌躇着。朱尼厄斯议员的住所可能是西莲山最大的房子,它的上层公寓有望和下层一样宽敞,然而,年轻的少年住在这里的许多周里,从来没有冒险探索它们。现在,一种焦虑的不安感浇灭了他的好奇心。
他肩上的渡鸦不安地抖动着羽毛,轻轻呱(croaked)了一声:“呱(Qua)!”
“安静点,卡波,”米南德低声道。“如果他们抓住了我们,把我们赶出去,我们就找不到她了……”
他正说着,绕过一个拐角,走进了一个点着火把的长廊——看见对面一扇禁闭大门的旁边,有两名魁梧的守卫。同时,守卫们也看见了他。米南德认为,他们既不像奴隶,也不像士兵,反而像专业斗士一样精瘦又坚强。每个人都披着深色斗篷,穿着无袖束腰外衣,腰间佩有一把短剑。
其中一人大步向前,低头盯着米南德。他的脸扭曲着,歪着嘴邪魅一笑,少年感到了一阵恐惧。
“滚开,矮子!”他怒吼道。“这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米南德赶快照办了。一会儿他就走出了走廊,下了楼梯。
“他们肯定把她关在那里了,卡波,”他嘀咕着。“来吧——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
他穿过阴影笼罩的中庭,走出一扇侧门,进入了一个狭窄的花园地带,然后沿着墙向房子后面走去。随着日落的接近,光线开始变暗。走了一段路程,米南德停下脚步,抬起头来。上面有一扇亮着的窗户,但是房子和周围墙壁之间的空间很小,少年无法退至远到能让他看见房间室内大部分情况的地方。
“卡波,请你飞上那里,好吗?”他低声说。“飞上去,看看她在不在。”
渡鸦展开它的大翅膀,重重地拍打着,飞上了二楼的窗户。它在窗台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飞回了原来的栖息地。
“你看见她了吗,卡波?”
“是的(Ita)¹!”鸟儿点了点头,呱呱叫道。
[注1:拉丁语,因此/就像的意思,卡波想表达的大概是就像你说的那样]
米南德点点头。“很好。回去等我吧。”
鸟儿照做了,男孩抓住了一个藤蔓棚架,藤蔓沿着房子粗糙的一面蜿蜒而上,伸向了分隔两层楼的窗台。
他决定用它来支撑体重,开始灵活地往上爬。不一会儿,他就到了窗户下面。他小心翼翼地把头探过窗台,费力地朝里看。他看到了一个家具齐全,挂着油灯照明的小房间。唯一的住户是一个年轻的黑发女人,她斜躺在沙发上,显然睡着了。
米南德感到自己的心在跳动,便滑过了窗台,与此同时,渡鸦又回到了他肩上。少年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注视着那个睡着的人。他意识到,她比他最初想象的要小,可能只比他大几岁——只是一个少女。柔和的灯光下,她精美绝伦的睡颜楚楚动人,米南德感到了一阵同情。
“哦,卡波,”他小声说,“我们不能让他能这么做……!”
房间突然变暗了一点。米南德转向窗户,如释重负地看到那只是一朵云,遮住了渐弱的阳光。他探出窗外。一阵冷风开始刮起来,一团参天的云正以惊人的速度从东方飘来。远处的云层下电闪着,短暂地照亮了远处的山丘和附近房屋的墙壁。滚滚雷声随着距离而减小。天更暗了,尽管米南德的视线被官邸后面的角落挡住了,但他还是意识到暴雨将偏离西莲山,很可能就在广场,在帕拉蒂尼,在卡匹托尔山朱庇特的伟大神庙上空爆发……
“西蒙!西蒙!”
听到少女的大声呼喊,米南德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来——看到她正坐在沙发上,双目圆睁地盯着空中。然后她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惊讶地盯着,张开嘴似乎又要大叫。米南德急忙走上前,并把一根手指放在他嘴前。“请——不要,”他低声说。
“你——你是谁?”
“我叫米南德,它是卡波。我们想成为你的朋友,但你必须让我们帮助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大喊西蒙的名字?”
少女怀疑地瞥了眼渡鸦,然后视线又回到那个穿着巫师袍的奇怪少年脸上。“为什么?你认识一个叫西蒙的人吗?”
“是的。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你会喜欢他的。希望他能在这里帮助我们。”
女孩盯着地板,微微皱起了眉头。“我梦到自己陷入了危险,但附近有人能帮我——一个我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的人。我对他说。他的名字是西蒙,但我也知道他的许多别名。我——我想不起来了——异象消失得太快了……”
“告诉我——你叫什么?”
“我叫海伦,住在伊奥尼亚的普罗迪科斯(Prodikos)¹家里。”少女的声音满是苦涩,她抬起眼睛,看向大门,眼中流露出恐惧。“那两个看门的畜生——他们绑架了我,把我带到了这里。现在我甚至比在父亲和主人家里还担心自己。告诉我,米南德,我会怎么样?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注1:Prodikos,在蒂尔尼的《星神之种(The Seed of the Star-God)》中登场过,是库伯勒(Cybele,小亚细亚的大母神,考虑到不是这篇内容,不多赘述)的信徒,但我不知道普罗迪科斯这个名字的来源,本以为是指苏格拉底的导师Πρόδικος,不过一个有点倾向于无神论,用自然主义解释宗教的人,怎么会去信仰库伯勒?时代也不对,所以应该只是蒂尔尼原创人物,Neta了这位智者的名字,或者刚好同名而已]
“我不能告诉你——没时间了。但西蒙会帮我们的,我知道他会的。别怕。我现在必须走了。我会偷些钱给你,这样你就能离开罗马,远走高飞,找些好人一起生活,我还会找到西蒙,把他带到这里,我们一起帮你逃跑。”
这么说着,米南德转向窗户,爬了出去。就在他开始沿藤而下之前,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女孩。她那闭月羞花的脸蛋上,混杂着困惑与希望。
“小心点,米南德,”她不安地低声说。
然后她回到了沙发上,试图坐下来泰然以待,却又越发担心,苦苦思索着,不一会儿,就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
西蒙在羊肠小道的阴影里停了下来,他跑上了山,所以气喘吁吁的。他强迫自己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听着,直到他不再喘着粗气,心跳也慢了下来。没有追赶的声音,但他隐约听到自己来时的路上传来了像是叱咤的喧闹声。西蒙咒骂着。残暴的狼群被唤醒,行动起来了,但愿他们找不到他的踪迹。
他又迈了几步,走到了朱尼厄斯花园的后墙边。在暮色中,他只能勉强辨认出大门。门是开着的。考虑到现在的时间,这是不寻常的,西蒙猜测卫兵们得到了命令,在他回来之前不能关门,或许他们就在里面等他。
然后他听到有人在吟唱低沉、单调的圣歌(a low, droning chant)。他意识到那一定是多西修斯,他在那个柱廊上等着献祭用的雕像和祭坛,吟诵着他最后的准备仪式。他听到的几句是波斯语,他听不懂,但他不止一次听到了阿兹达哈克这个名字,当他想起这个名字的含义时,他颤抖不已。尽管西蒙憎恨罗马,又感激多西修斯,他还是感到深恶痛绝,确信了自己不会参与即将到来的亵渎。
“海伦!”他喃喃道。“如果我没疯,而你确实在这里,他们就不能用你达成自己的目的!”
他小心翼翼地绕过大门,匆匆绕过墙角,进了一条羊肠小道。这里的阴影更深邃了。一会儿,西蒙小心摸索着,沿着墙走向了官邸的前面。突然,他听见头顶上传来一阵轻微的羽毛沙沙声,然后:
“西蒙!西蒙!”
他吓了一跳,但还是立刻听出了那低沉沙哑的呱呱声。他抬起头仔细看,看见了那只大鸟停在墙上,渐暗的天空中映衬着它的影子。
“卡波!你在这里干嘛?该死,是多西修斯派你来监视我的吗?”
鸟儿摇了摇头。“米南德!米南德!”它呱呱叫道。
西蒙蹲下身来,跳起来抓住了墙顶。他很轻松地爬了上去,然后轻轻落在里面的地上。渡鸦拍着翅膀飞了下来,停在了他肩上。
“呱!”它呱呱叫道,用喙指着离自己最近的那扇二楼窗户。“呱!”
“怎么了,卡波?那是什么?”
“光(Elán)!”
“光(Elán)——‘光(light)’,”西蒙喃喃着,不解地皱着眉头。然后:“等等!你是说——海伦(Helen)¹?”
[注1:Elán是爱尔兰语,与Helen一样,是光(light)的意思]
“是的!”
突然,一盏灯照亮了窗内的房间,西蒙看见一个苗条的年轻女子手里拿着一盏油灯,她从窗台上微微向外靠。似乎正在倾听,又或是试图窥探这夜空。她的脸被比夜晚本身还黑的长发所衬托,在灯光下显得苍白无力;她双目圆睁,似乎带着一缕不安,就像暗潭倒映着微弱的小火苗。
西蒙喘着粗气。是——她!
然后,他一动不动地蹲在墙的阴影里,发现自己在用嘴念她的名字——但是太小声了,就连肩上的渡鸦都听不见他的声音。
“米南德?卡波?”女孩的声音只是小心翼翼的呢喃,“是你们吗?”
西蒙动弹不得,也不能回答,但是卡波轻轻呱了一声,振翅高飞,停在了年轻女人旁边的窗台上,看到他,她似乎松了一口气。
“快点,米南德,”她说着,往下看着墙。
西蒙吃力地摆脱了让他一动不动的魔力,匆匆跑到了房边。他快速爬上了平开窗。得益于训练有素的肌肉,他毫不吃力,但他还是感到藤蔓略有松动,意识到了它们支撑不起比他更重的分量。过了一会儿,他爬上了窗台,站在这间房的大理石地板上。
女人退回了房间中间,目不转睛,却又毫不畏惧地打量着他。她的目光中似乎带有一种奇怪的惊喜。此时,西蒙在如此近的距离看着,发现她根本说不上是个女人,而是个或许最大也不超过十五岁的少女——他还发现她比那些国民都要年轻。尽管他一生中从未见过她,但他似乎熟知她秀色可餐形体和脸蛋的每一个轮廓。
“你!”他柔声喃喃道。“你……!”
“西蒙!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她把灯放在一张矮桌上,向他走来,西蒙也动身迎着她。一种奇妙又矛盾的情绪席卷了他。他感到狂喜与恐惧交织,不知何故,他觉得自己像是世界之主(the Lord of the World),正走向前接受世界的臣服,但同时又像是一个无力的祈祷者,走近了神(One)的圣坛,神的赞许给予了他宏伟力量(his lordly power)唯一的的生命与意义……¹
[注1:这段应该是在描述西蒙既是“父”又是“子”的设定]
突然,他怀里抱着一个年轻苗条的人类少女,她在他胸口啜泣,绝望地搂紧他,就像抓着风暴中的支柱。
“哦,西蒙!我是谁?你又是谁?”
“我不知道,”他安抚道。“我看到了一个你的异象……”
“我也梦到了你。西蒙——我们是谁?”
他把她从身边抱开,双手温柔地放在她肩上,注视着她如点漆的眼睛。他没有回答,因为没有必要。在那一瞬间,不知为何,他的意念似乎与她成了一体,不是合一,而是玄妙的相互理解。他一直认识她,她也一直认识他,一直在伟大的流变不真的物质世界(Illusion of Change)¹所有的未来轮转中,在爱与痛苦、恐惧与狂喜(ecstasy)中失去又找到对方,直到时间尽头的同一(Union)²……
[注1:Illusion of Change,在诺斯替里指物质世界流变不真]
[注2:Union,诺斯替主义中指施救者与被救者之间总体上的同一]
然后异象消失了,但理解却没有消失,西蒙知道这个少女已经和他分享了一切。
“真是奇怪!”她喃喃道。“我们只是人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万事万物竟然要在我们之内,通过我们才有唯一的意义,这怎么可能……?”
“我——我不知道,海伦。行邪术的多西修斯说一些人是真灵——神的灵魂(God-soul)碎片,被囚禁在了疯狂的恶魔阿卡穆特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里。”
“哦,西蒙!你说的当然是真的,我听以弗所阿尔忒弥斯(Artemis)¹的女祭司们说过这样的话——”
[注1:《约翰福音(The Acts of John)》中,在以弗所阿尔忒弥斯(希腊语:Ἄρτεμις、英语:Artemis)神庙的诞日,所有人都穿着白衣,只有使徒约翰穿着黑衣前往了神庙,他在那里向主祷告,约翰刚说完,神庙就毁灭了,阿尔忒弥斯的祭司被横梁砸死,以弗所的人们都皈依了约翰的神,之后约翰感知到祭司的亲戚希望约翰复活他,询问其是否如此,得到肯定答复后,就教导了这个年轻人,让他在尸体面前说“神的仆人约翰对你说,起来(引自张新樟编译本《古代诺斯替主义经典文集》)!”,年轻人照做,复活了祭司
部分观点认为,虽然阿尔忒弥斯是处女神,但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信仰,其实可能结合了库伯勒]
“等等——听!”
海伦闭上了嘴,突然害怕了起来,因为西蒙的声音很紧张——接着,通过窗口,她听到远处传来了许多嘈杂又愤怒的声音。
III
The wine of life is spilt upon the sand,
生命的醇酒泼洒在贫瘠的沙土,
My heart is as some famine-murdered land
我的内心就像灾难肆虐的土壤,
Whence all good things have perished utterly,
美好的事物已全部被斩尽杀光。
And well I know my soul in Hell must lie
我知道我的灵魂一定会进地狱,
If I this night before God’s throne should stand.
如果我今夜站立在神座的面前。
— Wilde, “E Tenebris”
——王尔德《走出黑暗》¹
[注1:引自袁宪军译本《玫瑰与芸香:王尔德诗选》]
西蒙突然转向窗户,大步走到窗前,探入了夜色中。“他们在集合——我想他们朝这里来了。那个该死的卫兵!我真不该提到朱尼厄斯议员的名字……”
海伦急忙走到他身边,听见远处似乎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声音,就像一群人在集合,渡鸦停在她旁边的窗台上,不安地躁动着、嘶鸣着,她心不在焉地抚摸着它,渡鸦渐渐静了下来,似乎得到了安慰。
“发生什么事了,西蒙?”她的声音平静却又不安。
就在那一瞬间,他还没来得及回答,房门咔嗒一声开了。西蒙和少女都意外地转了过去。两个豹头环眼的守卫进来了,他们中间的是——
“多西修斯!”西蒙咆哮道。色雷斯匕首已经被他拔出来,颤抖着握在手中了。
巫师注视着他,然后瞥了一眼海伦。他冷峻的脸上又露出一抹悲伤。
“我占卜到你在这里了,西蒙。你必须跟我来。是时候了。”
西蒙坚定地摇了摇头。“我欠你很多,多西修斯——事实上,就连我这条命也是欠你的。但在我做出你那该死的牺牲之前,我会让你把内脏都吐出来!”
“没用的,西蒙。你不得不为阿兹达哈克服务,因为你已经参加了仪式,被其所束缚。看呐。”撒玛利亚巫师向前走了一步,西蒙看见他伸出的掌心里有个东西,尺寸与形状都像鸽子蛋,乌黑发亮。上面闪着一些奇怪存在的轮廓图——一个骇人的龙头怪物,这造物(creature)¹肩上没长胳膊,取而代之的是两条蛇(serpents)²。就在西蒙疑惑自己是怎么能看清这么小图形的细节时,他感到了一阵强烈的恐惧。
[注1:creature,既有怪物的意思,又有造物的意思,大概是双关一下达哈卡与德缪歌被造物的身份]
[注2:偏历史化的版本,如《列王纪(波斯语:شاهنامه、英语:Shahnameh/Shahnama)》里,扎哈克被称为蛇王,就是因为其肩上长有两条黑蛇,但用serpents这个词,应该是缝合了一下德缪歌的狮头蛇身形象]
“哦,阿兹达哈克!”多西修斯呐喊着。“现在去领你的仆人(servant)吧!”
那个卵形物体跳出了巫师的手,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西蒙还没来得及反应,它就正中了他前额的中心!
马上,阵阵冰冷的疼痛刺穿了他,让他跪了下来。他尖叫着——但就在此时,疼痛已经消失了。他能感到那东西紧贴着他的额头,就像那些冰冷的巨大蜱虫。恐惧填满了他,他鼓起勇气,伸出手,想把它扯下来,却发现自己的手不听使唤。
“站起来,西蒙。”多西修斯说。
他照做了。他深陷的眼睛里一片阴翳,怨恨地瞪着行邪术者。他试图向前,却不能动。当他发现自己完全屈从于多西修斯的意志时,愤怒与绝望在他心中挣扎。
“西蒙!”他听到少女在尖叫,看到她惊恐地跑了过来,感到她张开双臂抱住了自己。“西蒙!”
多西修斯朝两个守卫点了点头,他们立即大步上前,粗暴地抓起少女的胳膊,她挣扎着、尖叫着,被拽出了房间。西蒙竭尽全力,疯狂地抵抗着控制了他的超自然力量——但他纹丝不动。
“哦,西蒙!”多西修斯低声道,悲伤与痛苦在他那双饱经沧桑的眼中一览无余。“你一定恨死我了!我能感受到你的憎恨、你的愤怒,甚至就像那些该下地狱的灵魂因为罪恶,感受到马兹达的烈焰焚烧一样。但是同情我吧,西蒙,这是我必须做的沉重之事。我多想死在你剑下的会是我,而不是那个美丽无辜的女仆,我很乐意用自己的生命摧毁那让全世界窒息的罗马暴政!但这不可能,只有一个崇高之魂(the High Soul)被其亲族(the Kindred One)¹杀死,才能诱导愤怒的诸神击杀祭拜者。同情我吧,西蒙,因为我体内的真灵,就和你的一样,同情着这个必须死的女孩——尽管你和她都会蒙受苦难,但这些却是真实的痛苦,最后将质变为其他物体。而我,由于参与献祭,最后必定为进入地狱(Hells),在那里忍受马兹达的烈焰,直到永远。”多西修斯的脸再次变得严峻起来。“不仅是这种,为了让提比略和他残酷的帝国走向灭亡,从而把所有国家从罗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我将忍受更多的痛苦!来吧,西蒙——到献祭的时间了。”
[注1:the Kindred One,指成对移涌中的另一个,或许也类似于诺斯替两个王子的情况,即一个救世主在地上完成使命期间,他的一个孪生兄弟或者永恒的救世主原型留在上界,最后二者会再次同一,高级的人性得到恢复,实际上在地上的人是外面的衣服,而在天上那个是里面的隐藏者,类似于高我,具体可以参考《多马行传(The Acts of Thomas)》中的《珍珠之歌(Hymn of the Pearl)》]
西蒙无可阻止,慢慢地跟着他憎恨的导师来到了点着火把的走廊,他感到离奇与疯狂,却又无力违抗……
身后空荡荡的房间里,传来了卡波羽毛的沙沙声,他在隐去自己身形的黑暗中动了起来,展开翅膀,从窗台上飞入了夜色之中。
米南德蹑手蹑脚地进入官邸的地窖,对自己看到的改变感到惊讶。火把比平时点的更多,但他、多西修斯和西蒙的东西都不在他们通常住的房间里。
他进入祭坛和雕像所在的房间,却发现它们都不见了。地板中间开着一个方形的洞——显然,之前祭坛藏起了这个洞。角落里有一个用厚篷帆布包起来的大包裹。少年走过去,看见上面有几张方形羊皮纸,羊皮纸被一张巨大的发黄卷轴压着。他认出了后者,因为多西修斯曾告诉过他那是什么:古代波斯的点火僧,奥斯当斯的《麻葛之智(Sapientia Magorum)》¹。
[注1:Sapientia Magorum,拉丁语,Sapientia是智慧的意思,Magorum是Magus的所有格,其实Magus就是Simon Magus那个Magus,二者的希腊语都是μìγος,因为在希腊人的眼里,麻葛就是群奇妙的魔法师,这个词源自于拜火教的麻葛,后来被用来指宽泛意义上的智者与魔法师,如后文的mage,词源就是magus]
他把卷轴和羊皮纸一起放在地上,检查着包裹,他解开其中一条绳子,微微展开了布。正如他所怀疑的,里面有更多卷轴,还有一些小瓶子和占卜工具——多西修斯的邪术装备——还有衣服和一点别的西蒙和他的东西。他把包裹全解开了——发现他要找的钱包不见了。
他又仓促地系上了包裹。很显然,多西修斯打算今晚就离开朱尼厄斯的官邸。他拿起卷轴,微微展开,瞥了一眼,他发现自己看不懂这种异乡文字,就赶紧把它又卷了起来。他记得多西修斯曾经说过,这是一本可怕又神秘的邪术汇编,即便是熟手,阅读亦或者试图使用,也依然很危险。
他把羊皮纸放在卷轴上,就在这时,他意识到它们是用希腊语写的——他曾被教导要像理解他的母语,阿拉米语一样,完美理解这种语言。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多西修斯自己的著作,显而易见地是对奥斯当斯卷轴的翻译或者详解。
“只有毫不犹豫、浑身是胆的行邪术者(读着最上面的羊皮纸上的字)才会召唤阿兹达哈克这个名字,那个因堕落(perversity)让存在(entity)陷入了物质混乱的邪恶者。然后,让他站在敌人的雕像前,献祭一个他真灵的对应者(True Spiritual Counterpart)¹,于是,被激怒的诸神就会用他们的愤怒杀死祭拜者。然而,无论献祭者的动机多么高尚,都要如履如临,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的准备仪式,都会聚齐那邪恶者的爪牙,就像秃鹫聚集在腐肉前一样。接着是行邪术者的生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除非他已经准备好在祭祀完后立刻逃跑了。但如果准备工作之后,没有完成献祭,那么,行邪术者的危险就更大了,因为这种情况下,阿胡拉·马兹达的右手,阿塔尔的火焰仆人,就会来报复阿兹达哈克的仆从们,彼时彼方,为邪恶服务者肯定会灭绝,与他们在一起的诸多无辜者也会死去,除非他们之中有一个纯洁的真灵,他将热忱(fervently)呼唤阿塔尔的名字……”
[注1:True Spiritual Counterpart,应该与the Kindred One一样]
突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米南德赶紧放下了羊皮纸,然后转过身去——看见约有十几个人挤在门口,男女皆有。他认出了他们,因为他们是朱尼厄斯家所有的奴隶和自由民。几乎所有人都拿着用布捆起来的包裹。
“快点!快点!”领头的高个子老人说,米南德认出了他是安布罗纽斯(Ambronius),朱尼厄斯的管家。“你们所有人都沿着地道往下走——它会把你们带到凯勒斯·维本纳(Caeles Vibenna)¹的废弃圣陵,自那以后,你们必须前往恩波里厄姆(Emporium)的港口,你们的女主人和其他人在船上等着,这艘船将把我们全都带到主人在安提乌姆(Antium)的庄园。快点——下来。等等——你们两个,吉多(Guido)和阿塞鲁斯(Asellus)——去拿那该死的外国行邪术者的包裹。就在这个角落里——啊!”他开始看到米南德站在指定的包裹旁后,就快步上前去。“年轻的巫师,你的导师在找你!他吩咐过我,如果我能找到你,就告诉你跟其他人一起离开这座房子。他晚点儿来找你会合。”
[注1:Caeles Vibenna/Caelius Vibenna,是生活在公元前750年(但是见下文)的一个伊特鲁里亚贵族,奥鲁斯·维本纳的兄弟。到达罗马后,维本纳帮助了罗慕路斯,参与了和提图斯·塔提乌斯的战争。]
“但是——我该去哪里?”米南德问。
“和这些人——朱尼厄斯家的最后一批人,一起穿过这地道。我主人(master)和我很快就会跟你们会合——如果你导师(master)的邪恶蛊惑(manipulations)没有很快把我们一网打尽的话。”
“我的导师并不邪恶!”米南德激动地反驳道。
“我的主人也是。”安布罗纽斯说道。“但恐怕朱尼厄斯议员的脑子已经被你的导师,多西修斯带进这座房子的疯狂之火烧坏了。”
“憎恨罗马是疯的?难道不是罗马把你变成奴隶的?”
老人的眼睛里燃起了痛苦与愤怒的火光。他收回手,好像要爆发,但随即就放了下来。
“朱尼厄斯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如果他按自己的方法来,没有人会成为主人或者奴隶!但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和一个这么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争论呢?按照你老师的吩咐,跟这些人一起穿过地道,在船上等我们吧。说起他——他让我把这些东西带走。”
这么说着,安布罗纽斯从包裹上夺走了卷轴和羊皮纸,就匆匆出了这个房间。
大多数奴隶已经从漆黑的洞口爬了下去,沿着密道消失了。只有两个人还留在这儿——两个穿着淡紫色无袖束腰外衣,看起来不比米南德大多少的年轻人。他们迅速捡起了厚篷帆布包,开始从洞口往下爬。
“快点,孩子。”其中一个喊道,然后从米南德的视线里消失了。
米南德快速赶到了洞口,朝下看去。两个年轻奴隶刚到井底,就用两支火把照亮了这竖井,它大约十英尺深。其中一个奴隶喊道:“撒玛利亚人,跟我们来。”他从支架上举起火把,两个人夹着包裹,消失在了水平的地道里。
“我——我来了,”米南德向井里大喊道。
然而,他不仅没有跟上,反而跳了起来,跑回地窖,赶向了楼梯,以便回到柱廊,他知道那里即将举行一场骇人的祭仪。
西蒙站在作为祭坛的石块前,右手紧握着他那不能自保的色雷斯匕首。海伦面朝他,坐在石头上,她天蓝色的无袖束腰外衣似乎被苍白的肤色衬得确实很暗。她因恐惧而瞠目。一种猛烈的绝望与愤怒在他心中肆虐。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让这个女孩免遭厄运;更想痛打并杀死这两个满脸横肉的守卫,他们正抓着她纤细的手臂;更想抓住他导师多西修斯消瘦的脖子,体验它被自己手指折断的感觉,就像折断腐烂的枯枝一样……
“西蒙,时间到了。”
是多西修斯——可憎的多西修斯的声音,西蒙曾觉得自己欠他一个人情。他看到老人走上前来,伸出了一只手,手里紧握着一个沉重的小袋子。
“拿着它,西蒙。这是钱——你要多少有多少的钱。今夜之后,你必须离开意大利。菲迪尼暴民的幸存者还记得你,如果你留在这儿,他们一定会找到你,把你杀了,但有了这些钱和朱尼厄斯的释放令,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远行了。我已经安排你去往帕提亚,越过罗马的统治,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跟随麻葛达拉莫斯(Magus Daramos)学习魔法。”这么说着,他向前弯腰,把小袋子系在了西蒙腰带上。
“等等!”其中一个抓着海伦的守卫大吼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报酬?我们为你服务得很好。把这个女孩绑到这里,可不是一般本领能做到的。”
多西修斯微微皱眉,接着点了点头。“好的。你们也会得到报酬的——仪式结束后马上给你们。”
“不,多西修斯——他们现在就会拿到报酬!”
多西修斯转身面向说话者,发现那是朱尼厄斯议员,他穿着绣有他官职象征的托加长袍,昂然又冷峻地站在那里。
“这些人现在就应该得到报酬,”朱尼厄斯重复道。“我会亲自付钱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离开。我已经决定了,我家里不能发生人祭。”
多西修斯怒视着他。“你疯了吗?”他咝咝呵斥道。
“没有。”朱尼厄斯摇了摇头,瞥了眼祭坛上的少女,又看回了多西修斯。“但我想,同意你这么做的时候,我是疯了。我和你一样憎恨罗马,我们都在它手中失去过亲人。但是听我说,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必须弄脏自己的手,甚至和奥古斯都那种暴君(Augustan tyrants)¹做过的一样吗?难道为了摧毁他们,我们就要变得和他们一样,夺走无辜的生命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
[注1:指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拉丁语:Gaius Octavius Augustus,公元前63年9月23日-公元14年8月19日),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Gaius Octavian Thurinus),后三头同盟之一,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元首,元首政制的创始人]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告诉过你……”
朱尼厄斯微微点头。“你告诉过我,如果我们举行不完仪式,那就很可能会发生灾难。我相信你。但现在我求你让这一切恢复原状,并用你的魔法来避免一切可能的恶果。即使在这提比略命令执法官,让公民们互相监视,并将同伴交给刽子手的邪恶时代,也并非所有罗马人都不值得尊重。我知道罗马的政治是肮脏的(vile),但现在我才知道邪术更肮脏。停止这一切,多西修斯。”
“我多希望可以停下来啊,但这只是痴心妄想!”多西修斯激动地摇着头,好像受到了折磨。“我知道你的真灵同情着这个女孩,就和我的一样。可我们不能退缩。现在回头太晚了。即使是现在,阿兹达哈克的邪恶爪牙也一定聚集在我们身边……”
“我在这里可感觉不到邪恶,”朱尼厄斯打断了他的话,“除了你准备举行的邪恶仪式。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种存在没有聚集呢?凡人的感官是迟钝的。在奥斯当斯那个时代,他是古波斯最伟大的麻葛(mage),他知道自己写了什么。我不知道阿兹达哈克爪牙的特征,但他们被描述成了世界上存在过的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极恶存在(the most vile and wicked beings),而我知道此时此刻,他们正聚集在我们身边。我们的仪式把他们引了过来,如果不举行献祭——继而把诸神的怒火从我们身上转移到祭拜者那里——上主马兹达(Lord Mazda)的火焰仆人将来杀光阿兹达哈克的仆从,连带着我们一起。”
“那我们全都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朱尼厄斯说道。“地道……”
就在这时,老安布罗纽斯从地窖里出来了。他走向了多西修斯,递给他了一张卷轴,还有一些方形羊皮纸。“这是你要的东西,撒玛利亚人。”
多西修斯点了点头,把卷轴塞进了他那饰有符号长袍的口袋里。
“安布罗纽斯,进屋去吧,”朱尼厄斯说道,“确保所有油灯和火把都熄灭了。我们都要立刻离开这里。”老奴离开柱廊后,朱尼厄斯再次转向了撒玛利亚巫师。“我不会动摇的,多西修斯。我家不应该成为人祭恶行的舞台。这些被雇佣的蠢货会拿到报酬,少女也会被释放。如果她愿意,我会把她接到家里,作我妻子的女仆。而你,多西修斯,将会得到丰厚的报酬……”
“愚蠢!”多西修斯后退一步,举起手,像是要行邪术。“你会这么轻易地放弃推翻奥古斯都式的暴政吗?我可不会!”他举起了其中一张羊皮纸,举到自己面前一臂之远的地方。“聆听我的呼唤,伟大的安哥拉·曼纽,恶之主(Lord of Evil)!现在把你最伟大的仆从送到我面前吧,他(Him)甚至创造了所有的物质世界!我用他的诸多名字召唤他:阿卡穆特、阿撒托斯、阿其路特(Aziluth)²、阿兹达哈克……”
[注2:Aziluth,原型世界(The Archetypal World),字面意思是“流溢的世界(the World of Emanation)”,卡巴拉生命树四个世界中最高的一个,被称为“接近神(near to God)”,代表着在我们对它的觉知之外、自性存在的现实本身]
“不!”
多西修斯听到这出其不意的大叫,转过身去——看到米南德在通往地窖的地板上的开口不远处站着。少年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忧虑,却又混杂着决心。多西修斯的脸沉了下来。
“你这个放肆的臭小鬼!为什么不跟着朱尼厄斯的奴隶们离开这所房子?”
少年被他导师不同寻常的厉声呵斥伤害到了,脸上流露出痛苦——但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了猛烈的振翅声。
“小心(Cavé)!”渡鸦尖叫着,向下飞进了点着火把的柱廊。“小心!”鸟儿在柱子和水池之间盘旋着,又叫了几次这个词,就落在米南德肩上休息了。
“卡波!”多西修斯大喊着。“有什么危险?告诉我……!”
就在这时,老安布罗纽斯跑进了柱廊。“有一大群暴民包围了这座房子!”他喊道。“他们甚至正在爬花园的墙,敲中庭的门。他们大吼着,强烈要求交出吉塔的西蒙。”
就在安布罗纽斯说话的时候,房间里的所有人开始听见屋外那些愤怒的咕哝声正在变得响亮——这种咕哝很快就大到成了愤怒的咆哮。
“我会处理好的,”朱尼厄斯厉声道。“来吧,安布罗纽斯。”
他们离开柱廊,连忙赶向了房子前面的中庭。多西修斯紧跟着,在门口停了下来。“来吧,西蒙,”他招手道。“我可能需要你高超的战斗本领。剩下的人留在这里。”
西蒙转身离开了海伦和祭坛,急忙追上导师,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如此自由地活动。显而易见的是,只要他服从多西修斯的意志,就不会被束缚。
他们四人聚齐到中庭时,巨大的撞击声在那里回荡着。外门承受了大量拳打与棍击,幸有两个厚实的门闩锁住了它们。被压低了的喊叫声渗了进来:“交出角斗士!交出吉塔的西蒙!”
“人渣!”朱尼厄斯咕哝道。“他们怎么敢袭击我的房子!是想跟我对质吗?那就来吧,听听我对他们的看法。”
“别开门,”多西修斯警告道。他担心庇护人身为贵族的愤懑会让他做出不明智的举动。“如果一定要跟他们讲话,那你至少要在楼上的窗前,在那里你能俯视他们,也能更好地判断他们的脾气。”
朱尼厄斯瞪了他一眼,但又点了点头。老安布罗纽斯赶紧领着他们三个出了中庭,上了二楼,绕向一扇可以俯瞰前门的窗户。西蒙在殿后,他经常尝试回头,却又做不到。
终于,他们全都站在一扇宽大的平开窗前。安布罗纽斯敞开了百叶窗,他们向外望去。
“吉塔的西蒙!”吼声如雷贯耳。“角斗士西蒙!行邪术的西蒙!把他交给我们!”
西蒙俯视着挤在狭窄的街巷里汹涌的那群暴民,俯视着拥挤的火把、满脸的苦大仇深与举起来威胁的拳头。他们有数百——不,数千人——还有更多的人在聚集。暴民——罗马暴民——渴望着复仇,渴望着鲜血……
“交出朱尼厄斯!”他们喊着口号。“交出背信弃义的朱尼厄斯!交出叛徒和他那窝行邪术者!”
西蒙瞥了一眼朱尼厄斯,在他眼中看到了与自己类似的恐惧。他又看向那群暴民——喊着口号、大叫着的罗马暴民,他们挥舞着火把、拳头、剑、大头棒与匕首——他在竞技场上为活命而战时,他们也曾幸灾乐祸地欢呼。他看到人群的边缘,已经有一群群人冲进了邻居们的家里,在里面洗劫、强奸与杀戮……
“他们已经疯了!”朱尼厄斯喊道。
暴民们注意到了这四个人正从平开窗往外看,突然加大了吼声。诸如石头、箭矢与土块之类的飞弹撞进了房间。西蒙和多西修斯本能地后退了,安布罗纽斯抓紧了主人的肩膀,把他拽离窗前,然后赶紧关上并锁住了百叶窗。重物撞击防护板的声音回荡着。
“交出行邪术的西蒙!”暴民们被压低的叫喊声传了进来。“交出背信弃义的朱尼厄斯!”
“疯了!”朱尼厄斯低声道,显然是被吓到了。
“啊!”理解的霞光在多西修斯脸上破晓。“疯狂——与邪恶!我早该猜到的——这世上还有什么是能比罗马暴民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恶呢?这些阿兹达哈克的爪牙在不知不觉中,被行过的咒语引了过来。现在他们渴望鲜血与消遣,就像在竞技场上一样。快点——回到柱廊!你,安布罗纽斯,守着前面的入口。我们必须完成献祭,然后在这群疯子冲进来之前,通过地道逃跑。”
IV
What if the breath that kindled those grim fires,
吹燃那些沉眠中无情之火的呼吸,
Awaked, should blow them into sevenfold rage,
如把它们吹成七倍的愤怒,
And plunge us in the flames; or from above
把我们投进呼啦啦的火焰,那又该怎样?
Should intermitted vengeance arm again
或者他的红血右手把灾祸降落我们头上,
His red right hand to plague us? What if all
重新武装那中断的报复,那又应该怎样?
Her stories were opened, and this firmament
如果她所有的仓库全都打开,
Of hell should spout her cataracts of fire…?
地狱之天喷出她瀑布般的烈火……?
— Milton, “Paradise Lost”
——弥尔顿《失乐园》¹
[注1:引自刘捷译本《失乐园》]
他们四个连忙下楼时,西蒙再次因无能为力而感到了绝望。他渴望拽掉那个附着于他额头上的冰冷又邪恶的符咒(the cold, evil talisman)¹——然后把剑刃插入多西修斯的后背。然而这两件事他都做不到,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但身体动作却不是。
[注1:简单来说,虽然talisman指的是会给人带来好运的护身符,但《旧约》认为护身符是邪恶的迷信,只有信仰偶像之人才会佩戴]
一会儿,除了安布罗纽斯,他们都又回到了柱廊。西蒙看见海伦苍白无力地昏倒了,她正跪在地上,守卫解开了她的无袖束腰外衣,让她露出腰部以上,多西修斯招手示意之后,他们把她拉了起来,让她向后弯,放在了祭坛冰冷的石头上,等待着匕首的一击。他们后面立着提比略的灰色雕像,火把摇曳的微光之下,它的脸色残酷又阴森。西蒙的怒火加倍燃烧着,他感到自己的心和头都在怦怦直跳,像是要炸开。他索然无味地注意到米南德在一旁站着,年轻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忧虑,渡鸦在他肩上成了一道黑影。
“很好,”多西修斯低语道。“现在,仪式……”
“不!”朱尼厄斯大喊道。“我们必须从地道逃走,别再疯了,多西修斯——让提比略和该死的罗马暴民做他们想做的……”
多西修斯没有理会议员,他举起了双手,又开始吟唱起了那可怕的咒语:“聆听我的呼唤,伟大的安哥拉·曼纽,恶之主……”
朱尼厄斯感到了一阵寒意,一种让人麻痹的恐惧,不知怎的,他感到强大的超自然力量违背了他的意志,让他犹豫不决、踌躇不前。西蒙也感觉到了——当他拿匕首的手臂开始举起来的时候,他甚至感受到了更强烈的恐惧。多西修斯吟诵着那极度可怕的力量之名(Name of Power)的不同变体,西蒙知道,再过一会儿,他就会被迫把西卡的剑刃刺入少女的胸膛。
“……阿其路特、阿兹达哈克……”
米南德也感到了恐惧,但同时,他又回想起了在羊皮纸上读到的字。他热忱地希望自己符合要求,于是竭尽全力地大喊着:
“阿塔尔!”
西蒙感到胳膊停了下来。多西修斯停止了吟唱,眼中闪过一丝恐惧。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极度的紧张感……
突然,渡鸦从米南德肩上一跃而起。“阿塔尔!”它尖叫着,绕着柱廊狂热地拍打着翅膀。“阿塔尔!阿塔尔!”接着,它毫无征兆地停止了疯狂的盘旋,猛地俯冲向了西蒙的头部。西蒙听到卡波沉重的喙啪嗒啪嗒地分开了他与前额上的黑色卵形物,西蒙喘着粗气——感觉就像核桃从茎上被拔下来。然后他听到鸟儿飞走了,听到它放下那个东西时刺耳的嘎嘎声,听到那个东西溅入柱廊的水池里……
西蒙大肆咆哮。他自由了!他立刻打出了多西修斯意志所驱使的那一击——但色雷斯匕首锋利的剑刃没有刺入海伦的胸膛,而是深深地刺入了一个绑架她的人的心脏!
“不!”多西修斯尖叫着。
受伤的守卫一声不吭地倒下了。另一个马上放了海伦,跳了回去,拔出他的罗马短剑。西蒙狂怒地咆哮着,跃过了倒下的少女与祭坛,向他扑来。双刃齐鸣,火花四溅。受雇的绑匪退得更远了,他突然瞠着目,因为他意识到了敌人的实力。尽管他的战斗技巧很专业,但他并没有像西蒙那样,在竞技场上为了活命而奋斗两年。他也从未面对过这么愤怒的对手。
“朱尼厄斯。”守卫尖叫着。“多西修斯!叫你们的狗停下来!”
就在那一刻,西蒙扑向了他敌人的守卫,凶恶的色雷斯剑刃划开了他腹部的血肉,摩擦着他的脊椎骨。绑匪四仰八叉,重重地倒在石头地板上,在濒死的痛苦中不停发出漱口声,鲜血如洪水般从他巨大的伤口中喷涌而出。
西蒙转着圈,蹲伏着,好像在期待着另一个敌人,他红匕紧握,泰然地准备着攻击。透过一片绯红之雾,他看见其他人都惊恐地盯着他:朱尼厄斯、年轻的米南德与再次停在他肩上的渡鸦、海伦虚弱地靠在祭坛上,还有——
“多西修斯!”
西蒙说到这个名字时,发出的是一种低沉的咝咝声。然后,他漆黑的眼睛像正在狩猎的野兽一样亮了起来,他开始前进……
突然,就在那一瞬间,轰隆的撞击声回荡在整座房子里。一时之间,每个人都僵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他们的眼睛都转向了房子的前面,撞击的回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接着又是一声巨响,混杂着木头裂成片的声音。
安布罗纽斯冲进了柱廊。“暴民们闯进来了!”他大喊着。“他们造了一个攻城锤,把前门砸开了。我们必须逃了!”
“小心!”渡鸦尖叫着。西蒙瞥了它一眼,它潜入了通往地窖的洞口,就像一团黑色的羽毛俯冲而下。他站在那里,一时间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跑向海伦,还是该按照计划,把多西修斯打个半死。令人惊讶的是,老巫师正盯着闪烁在柱廊上空的群星。
“卡波知道!”他大吼着。“他们来了——阿兹达哈克的爪牙!快点,你们所有人——地道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西蒙向上瞥着,看见接近天顶的地方,有一簇簇比普通的星星还亮的黄光。他们似乎在闲逛、转悠、越来越亮、越来越近。然后他听到了脚步声,就向下看,发现多西修斯和米南德从地窖的台阶上消失了。朱尼厄斯和安布罗纽斯扶着海伦站起来,好让她快点走向楼梯。
“西蒙!”多西修斯大叫着,在他消失的同时。“快点!”
宅邸前面传来了一声撞碎的回响——随之而来的喧嚣骚动,让西蒙意识到暴民们已经闯进来了。又一声撞击回荡着,这一声是从房子后面通往花园的短廊里传来的。转瞬之间,形形色色的一丘之貉涌进了柱廊——一群虎视眈眈,挥舞着石头、棍棒与匕首的劫掠者。
西蒙捡起了倒下敌人的一把短剑,然后向海伦与其他人刚刚消失的洞口跳去。
“就是他!”其中一个闯入者尖叫着。“是角斗士西蒙——行邪术的西蒙!”
西蒙跳进了地窖的洞口,落在第三级台阶上,他伸手抓住了靠墙的沉重地板门的圆环。它嘎吱作响,在生锈的铰链上缓缓移动。一块砖砸在上面,差一点砸中他的头。他疯狂地咒骂着巴力,把全身的蛮力都使了出去,久未使用的铰链投降了,伴随着一声巨响,厚重的石板倒下了。
西蒙滚下了几级台阶,他身边的剑与匕首与石头碰撞,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才让他得以停下来。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收拾好武器,感谢巴力没有让它们的剑刃伤到他。在楼梯脚下,他发现其他人都在抬头看着他。上面,厚重的石板回荡着重击的声音。
“快点!”西蒙大喊着,与他们会合。“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想出办法撬开那扇门。等等——你们走的时候带上所有点燃的火把。别让他们太简单了。”
几分钟后,他们都聚齐在地道口所在的小房间里。头顶传来了低声的叫嚷与重重的脚步声,暴民们如暴风雨般肆虐了朱尼厄斯议员的官邸,劫掠着、破坏着。然后叫嚷声越来越大,有种回音的感觉,西蒙意识到地窖的门被粗暴地破开了。
“你们所有人,都进地道去!”他咆哮着。“把所有不需要的火把都熄灭,剩下的带走。”
他们很快就照办完了。多西修斯先走一步,朱尼厄斯带着海伦从上面下来时,安布罗纽斯留下来帮她下去。议员后面是米南德,但是少年抓紧铁扶手停了下来,抬头担心地盯着西蒙。
“卡波在哪里?”
“如果我了解他的话,他现在已经在地道尽头了,”西蒙说道。“你最好也上路。快点——其他人已经出发了……”
“西蒙!你不跟来吗?”
“我当然会跟上。出发吧,该死的!”
米南德钻下了竖井,从支架上拿起了最后一支点燃的火把,就赶快下了地道。
西蒙转身背向洞口,直面着通往地窖其他部分的黑暗大门。吵闹声越来越大,显而易见的是,暴民们正摸索着下楼,一会儿,他们就会找到自己的火把,他们会冲进这个地方,大吼着要血,贪婪地掠夺贮藏的酒食,寻找女人消遣、玩他们的强奸游戏……
他们还会找到地道,因为曾盖住它的石坛已经被挪到了柱廊。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地道,其他人逃不掉了——海伦逃不掉了——除非他,西蒙,留下来捍卫它。为了捍卫它,也为了带着每个该死的罗马人与他一起走向毁灭……
吵闹声近了,他开始感到了远处火把的光亮。他迅速转身,准备把自己的火把扔进竖井去,但愿它的光还没被看见——他发现火把完全照亮了一张正从井里探出来的花白的脸。
“多西修斯!”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干嘛~哈哈~哎呦(What in the Hells)……!”
“不要扔掉你的火把。”老人急不可耐地说道。“你会需要它的。它是黑暗之海中的星星之火。”
“滚出这儿!”西蒙咆哮道。“你会把罗马人领到其他人那里吗……?”
“你是说,到海伦那里。别怕,她和其他人都在顺着地道全速逃跑。我告诉过他们,我是为你而回的——但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俩都很可能死在这里。”
西蒙举起了罗马短剑,好像要攻击,但随即就放了下来,因为他看到多西修斯并没有采取任何手段,去保护他那可敬的头。老巫师的眼里充满了悲伤与忧虑。
“把你的火把给我,西蒙,”他说道。“它是我们唯一的自救机会——或者至少拖延一下我们的敌人,让海伦和其他人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叫喊与咒骂从远处的地窖传来,西蒙意识到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他火把的光亮。他快速地把火把塞进了多西修斯举起的手,一边转身面向门口,一边拔出了他的西卡。
“你最好是胜券在握,巫师!”他咆哮着,双手寒光闪闪。
大量跑动与愤怒的喧闹声随之而来。然后,全副武装人群的身影浮现在门口,拥挤着、努力着,想要涌进来。他们怒目而视,眼中火冒三丈,在他们身后,一群被仇恨扭曲了面孔人闹闹哄哄,挥舞着火把、匕首与棍棒。
“交出角斗士西蒙!”他们疯狂地尖叫着。“交出行邪术的西蒙!”
门的宽度只能容纳两人并排而行,西蒙拿着兵器迎上了前两个人,熟练地招架、劈砍与刺击。一个被剑捅入腹部,受了致命一击而倒下;另一个跳了回去,突然感到了恐惧,却又被暴民们涌上前去——死在了西卡的剑尖上。西蒙大肆怒吼,挥舞并刺击着,一根大头棒狠狠地擦过了西蒙的左肩,一点刀锋割开了他的肋骨,但又有三个敌人喷洒着鲜血,倒在了地上。一杆长矛划破了他的无袖束腰外衣,划开了他的一侧胸腔。他咆哮着,用力还击,用剑劈开了一张怒吼着的脸。一种若狂的欣喜充满了他的身心,如果他必须死,他更喜欢与罗马人血战到底这种结局。
“阿塔尔!”他突然听见了多西修斯的尖叫。“来吧,哦,马兹达的伟大仆人!”
一根棍子啪的一声,打在了西蒙的左手腕上,让他的短剑掉在了地上。他的色雷斯匕首立刻给攻击者的脖子划了道线,但涌动的人群依然增加着西蒙的压力……
“来吧,哦,马兹达的仆人——带着你的净化之火来吧!”
突然,一道耀眼的白光照彻房间,从西蒙身边洒出了门口。在那一瞬间,离他最近的敌人被万丈光芒照射,似乎变成了白垩。人群中响起了一声尖叫,他们统统往后退。西蒙偷偷看了一眼身后,发现多西修斯高举的手中燃起了怒火,火把上闪着一簇刺目的蓝白光芒,老人的眼睛紧闭着——他马上转了回去,以免被闪瞎。他的敌人们仍在从门口往后退。然后,从他们的惊声尖叫中,他听出了不少远处传来的低声,明显是从楼上传来的,一起的还有许多雷鸣般的踩踏声,就像是一大群人在恐惧之中仓皇出逃。
“来吧,伟大的阿塔尔!”多西修斯尖叫道。“给阿兹达哈克的爪牙们带来灾殃吧!”
西蒙感觉到,在暴民们的火把、烈焰与挥舞着的兵器那边,从地窖的远处传来了一簇越来越强的火光。地窖的入口好像在变亮,仿佛打开了一个大火炉的炉口。恐惧的叫喊从人群后面传来,但最前面的人们又开始了前冲。
“让开,西蒙——快点!”多西修斯大喊道。
西蒙出于本能地跳到了门边。瞬间,一道流星般的白色强光掠过了他,多西修斯把邪术点燃的火把扔出了门,扔进了暴民之中。超过一百人的喉咙里涌出了震耳欲聋的惊声尖叫。
西蒙看见多西修斯向他招手,然后消失在了竖井之中。他赶紧来到井边,把西卡插入鞘里,接着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门外整个地窖都被耀眼的白光洪流淹没了。暴民们手中的火把都点燃了,膨胀成了似乎在蠕动、骇人且有意识的烈焰存在——与此同时,在地窖入口那边,火光更亮了,像钢水瀑布一样,顺流淹没了楼梯。人群疯狂地转来转去,在痛苦与恐惧中尖叫着,如同罪人的灵魂突然被囚禁在地狱(Hell)的坑里。
西蒙跳进了竖井,仓促之间,他几乎没碰到铁扶手。脚落地时,他听见多西修斯沿着水平的地道飞奔而下,就赶紧追了上去。这里一片漆黑——西蒙在上面目睹过火光之后,黑暗更是加倍了。
“快点——别停,”他听见多西修斯往回喊。“我们正处在烈焰仆人们带来的巨大危机之中。”
“该死,我们会在黑暗中摔倒的……!”西蒙咆哮着。
“不。这条地道又直又平。朱尼厄斯告诉我,它是数个世纪以前建成的,当时西莲山被用来抵御高卢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进攻。它会把我们带往凯勒斯·维本纳的圣陵——它在暴民们追击范围之外,但愿吧。从那里我们可以去到山脚下,然后前往恩波里厄姆,朱尼厄斯的船在那里等着我们,它会把我们带到安提乌姆。但是要快!”
西蒙尽可能快地向前摸索了几分钟,伸出双手摸着两边的墙,他听见了多西修斯在前面不远处蹒跚着喘气。接着,他似乎开始能看清一点了。往回瞥了一眼,他意识到有股可怕的刺眼光芒开始渗透了身后的地道。
“马兹达保佑我们!”多西修斯喘着粗气,因为他意识到了光线。“再快点!西蒙!跑!”
“那是什么?”
“阿塔尔的火焰仆人之一。他看见我召唤他的地方了,现在他跟着我们。”
西蒙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有个巨大的火球填满了地道的另一边。火球瞬间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大。一种奇怪的嗡嗡声与噼啪声遍布了空气。
“快点!”多西修斯喊着。
他们又走了几步,就到了地道的尽头:通过身后的危险火光,西蒙看清了地道。老多西修斯上气不接下气,步履蹒跚,踉踉跄跄的。
“我爬不出去了,西蒙。快点上去,把石板推好。那东西不能穿过石头……”
西蒙发现方洞与地道顶齐平。他猛地一跳,轻而易举地上去了,他平躺在地板上,向下伸手,抓紧了多西修斯的一只胳膊。通道里的火光越来越强,嗡嗡声越来越响。
“地板门,西蒙!”老巫师喘着粗气道。“这是你唯一的机会。离开我……”
随着力量上涌,西蒙提起了他的导师,把他粗暴地拽到了坑边。石门靠古老的铰链打开,就和朱尼厄斯柱廊的那扇一样。白色火光从坑里照了出来。西蒙用尽全身力气关门,他看到身下地道里的火海开始沸腾,熊熊烈火成卷须状,火光照彻天地,听见嗡嗡声变大了,成了尖锐的怒吼……
然后,门咔嚓一声,重重地落回了原处。黑暗又一次君临。下面传来了小声的嗡嗡。不知怎的,西蒙想起了困住巨大(monstrous)马蜂的蜂巢。他的手还放在石头上面,它似乎突然变暖了,他连忙起身往回赶。
多西修斯在黑暗中醒来。西蒙的眼睛适应黑暗后,发现他们站在一个不怎么深的天然石窟里,前面堆砌着柱子和门楣。他们身后立着一尊接近真人大小的石雕,男人穿着古罗马战士的服装。远处是漆黑的夜空,却燃起了璀璨的火光。
“快点,西蒙,”多西修斯喘着气。“我们的危机还没有解除。那东西会顺着地道返回地窖,然后来到这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他们赶紧离开了小圣陵,顺着台阶下去,到了一条狭窄的街道,避开那亮闪闪的强光,他们知道,这光芒是从远处山上烧着的房屋传来的。暴民们并没有波及到这里,但他们可以听到不远处——人们的惊声尖叫。偶尔会有闪光驱散黑暗,但西蒙忍住了回望的诱惑。他知道那是非人的天降之物——火与复仇的存在前来净化地球上的凶恶邪术,烧毁(consume)阿兹达哈克的堕落仆从。
他们沿着一片黑暗的狭窄小巷逃跑,西蒙一多半时间都背着他年迈的导师。他们遇见的人寥寥无几,那几个人也没注意到他们,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山上蔓延的火海上。
最后,这对逃亡者上气不接下气地停在了帕巴托(Pabato)之线脚下的一条大街上,他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来路——他们回头瞥了一眼,都畏惧地(awe)大叫了起来。整个西莲山的上半部分都被沸腾的滔天火海淹没了,在朱尼厄斯宅邸所在的那片区域,成群结队的明亮光球飞来飞去——他们有几百个,俯冲着、下降着、高飞着。他们每到一处,就会有新的火苗窜出。
远处隐隐传来了一种声音——整座山被烈焰包围并吞没,成千上万人死去的可怕声音。霎时间,西蒙感到了一阵恐惧的战栗,忘记了他对罗马的仇恨,罗马杀害了他的父母,把他强行带入了角斗场的残酷奴役。罗马人们正在死去,但死去的不只是投机取巧的愤怒暴民,也不只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残忍虐待狂卫兵。人们正在死去——主人和奴隶、贵族和工人、商人和流浪儿、妇女和儿童……不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多好或者有多坏,大火都对他们一视同仁,毁灭殆尽。
“马兹达之火,”多西修斯喃喃道,“正在净化阿兹达哈克在地球上的堕落爪牙。”
西蒙转向了他,发现远处的地狱火海倒映在他那苍老的乌珠里。多西修斯察觉到了学徒的目光,面向他,发现西蒙手中紧握着色雷斯匕首,像是要拔出来。
“你说那些罗马人是邪恶者的爪牙,”西蒙忐忑不安,说道。“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不也是这种爪牙吗——其他所有人类不也是?如果是这样,马兹达,光之主不是挺乐意看我们这些堕落的存在自相残杀的吗——就像我打算现在就杀了你一样?”
多西修斯叹了口气。“杀吧,我不在乎,因为我累了。我走了歧路,以为一个错误会带来更伟大的正确——以为对一个奴隶女孩的不公会让数百万人摆脱罗马的不公。好吧,诸神的旨意不同,我和我所有的计划都失败了。但是在你打死我之前,西蒙,请你仔细想想:如果你像我无知时想让你做的那样,杀死了海伦,光之主会高兴吗?”
西蒙叹了口气,就和多西修斯一样,然后沮丧地摇了摇头。“不用担心你的命,老导师。因为一些原因,我已经不再能做到憎恨你了。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海伦呢?”
多西修斯皱眉沉思。“海伦跟着朱尼厄斯议员,去了他在安提乌姆的家里,她很安全。我们也会去那里待一段时间——但如果你还想让我当你导师的话,我们必须离开罗马,去帕提亚寻求庇护。米南德和卡波也会跟着,但你必须让海伦留下。”
“我做不到!”西蒙生气地说——但正是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似乎感到命运之手在向他逼近。
“哦,西蒙,原谅我吧!”老巫师眼中突然闪起了悲伤,甚至是悲痛的光芒。“曾经我也被迫失去了一个真灵的对应者。罗马人杀了她。但是你——你可以离开这儿,因为你知道你的对应者还活着,她会等着你今生归来,而不是等下辈子。恐怕是我那误入歧途的魔法让你们在诸神意愿之前走到了一起,所以你们现在必须分开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复仇的暴民很快就会掘地三尺,试图再一次追捕你,西蒙,除非你离开罗马。只有时间的流逝能让你在这里成为无名之辈。”
西蒙感觉这是真的。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凯里乌斯之山(the Mount of Caelius),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死于熊熊燃烧的烈火,然后抬头看,那里的星星在黑色的天空中,漠不关心地照耀着下方。现在,一群闪闪发光的球体(globes)正迅速消失在天顶,暗淡着、消失着,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一看到他们,西蒙就浑身冷颤。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再次见到海伦,不久之后,一扇旅行、学习和自由的生活大门将会向他打开——然而,他所有的感情都染上了一层沮丧。骇人的存在为宇宙的权力而争斗,力求分开真灵们,或者将他们重新同一成光之主,他知道这些知识将让他永远远离普通的幸福与满足,他投身于永恒之战(Eternal Struggle)。
“走吧——去恩波里厄姆,去安提乌姆,”西蒙说道,他扶着步履蹒跚的多西修斯,走过黑暗的街道。两人都没有再回头看一眼,那里高耸的火焰照彻天地,怒视着夜晚的黑暗。
【END】
上一篇:暴雨黄色预警继续!贵州湖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下一篇:最后一页
-

焦点要闻:译文:马兹达之火——理查德·L·蒂尔尼
原名:TheFireofMazda译者:美亚未经译者允许,禁止无端转载前注:篇名
-

国企一把手收受124万被判4年,因一次饭局心理失衡
6月16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廉洁四川”披露了这起典型案例,凉山州宁南
-

“吊丝三宝”感觉要凉凉了,五月份B级车销量公布:无一款过千辆-全球视讯
导读:近日,“乘联会”公布了五月份的B级车销量排名,从整个榜单来整体
-

暴雨黄色预警继续!贵州湖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暴雨黄色预警继续!贵州湖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
-

每日热议!美国大选支持率最新统计_2020美国大选支持率最新
第1位网友观点:3月27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公布了最近的一次民意
-

全球球精选!北京第三座大悦城开业 由大悦城控股联合华远地产打造
观点网讯:6月18日,作为北京第三座大悦城,京西大悦城开业亮相。据观
-

环球报道:qq游戏英雄杀挂 qq英雄杀外挂
1、没有这个英雄哦。2、只有靠楼主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猜出来哦。3、再
-

oppok5手机什么时候上市的_oppok5手机什么时候上市
1、Oppok5手机于2019年10月17日上市。OPPOK5是首款搭载VOOC4 0的OPPO手机。采用640
-

即时焦点:私人借条模板
私人借条模板(精选3篇)私人借条模板篇1今A借给B人民币壹万元整,即¥
-

河北一男子疑招工被骗失联,家属:曾打电话说被卖到缅甸,需25万赎人|世界最新
河北一男子疑招工被骗失联,家属:曾打电话说被卖到缅甸,需25万赎人6
-

全球快资讯: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科研成果展示 |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研究与应用-环球观天下
首席专家:闫江闫江教授,北方工业大学高精尖创新研究院院长,国家级人
-

世界信息:跨省存款火了:存50万5年下来差价5000
跨省存款突然火了,“60元车费,多赚几千元” 近日,继六大行集体下
-

今日热文:白酒价格大面积倒挂,线上比线下更严重,多家酒企调价控货
对于白酒行业接下来的库存发展,相关预计,2023年中秋可将渠道库存去化
-

尼康d810和d850比较哪个性能更优_尼康d810与d850比较 当前快讯
1、目前来说,D810除了价格便宜之外,就没啥优势了。2、而且,既然选择
-

贵州黄平一女生遭校园霸凌被多人掌掴?警方已介入调查
6月18日,有网友报料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中学发生一
-

大四男生实习薪资1万4妈妈仰天大笑,网友:我1万4笑得比阿姨还大声
据@白鹿视频,近日,福建福州。有网友看了视频评论道:“我1万4笑得比
-

视频 | 2023新疆网络文化节 乌鲁木齐“丝路礼物”电商文化节启动_每日快报
6月18日,2023新疆网络文化节|乌鲁木齐“丝路礼物”电商文化节在十九省
-

真子集的符号如何在word上发出来_真子集的符号_世界速看料
1、打开 " "Word "文档后在“插入”下拉菜单里选择对象,然后出现“对
-

世界观热点:变异汪星人3怎么得猫_变异汪星人3选猫
1、本地游戏无法获得猫,得玩能联网的,游戏开始选择ONLINESAVE,然后注
-

除了独库公路,新疆还能怎么玩? 天天热文
除了独库公路,新疆还能怎么玩?
X 关闭
X 关闭
-
浙江杭州推动智能家居产业链提升 让家变得更“聪明”
06-18 21:21:16
-
烧烤经济火爆啤酒进口大增 5月我省啤酒进口8816万元
06-18 20:34:41
-
焦点观察:肺结节有啥症状_良性肺结节有什么症状
06-18 20:05:40
-
经典动漫《浪客剑心》新作预告公开 将于7月6日在各大电视台开播
06-18 20:06:58
-
盖尔·加朵主演间谍惊悚片《铁石心肠》发布正式预告 将于8月11日上线
06-18 20:05:16
- 苹果当然表示将不再报告iPhone的销售数字
- 球场变“池塘”!中甲雨战广州队失点,1-1无锡吴钩,无缘2连胜|全球快资讯
- 快消息!广末凉子丈夫为妻子出轨公开道歉:她是个好妻子,最努力、最优秀
- 贵州一女生遭校园霸凌被多人掌掴?警方介入 围观学生边抽烟边拍摄
- 江苏:多地低山丘岗地区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 焦点速讯:聚焦健康食品博览会丨食品企业供需对接 签约金额超102亿元
- 【天天播资讯】重庆:赛舟比拼迎端午
- 世界看热讯:台湾省芯片制造需要砂子,从大陆进口占九成,为何台湾不怕制裁?
- 城管拆除商家招牌称易起火却无法点燃-环球消息
- 每日快看:6月19日起 集美新增两条接驳线
- 跨省存款火了:存50万差价5000 专家发声回应:合规!
- 全球观焦点:南疆行记(四)塔莎古道
- 全球微速讯:iQOO 11S手机曝光 骁龙8 Gen2+200W快充
- 百事通!中国驻伊朗使馆: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防范盗抢案件
- 女导游穿“紧身裤”是色情营销?色的究竟是谁 环球今亮点
- 重庆云阳一处山体危岩垮塌 附近村民紧急撤离|世界消息
- 75b内衣对应尺码有多大_75b内衣对应尺码
- 今天,山海城市体育公园开园啦!_焦点热闻
- 天天亮点!为排海做铺垫?日本东电7月起将允许民众参观福岛第一核电站
- 快消息!2023年小麦相关上市公司有哪些?(6月18日)
- 全球动态:红色对战平台(se对战平台)
- 金山这个安置房项目有新进展,预计交付时间→ 世界热点评
- 柏官庄村_关于柏官庄村概略
- 好紧张!多地高考评卷现场曝光!
- 热推荐:2023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在厦门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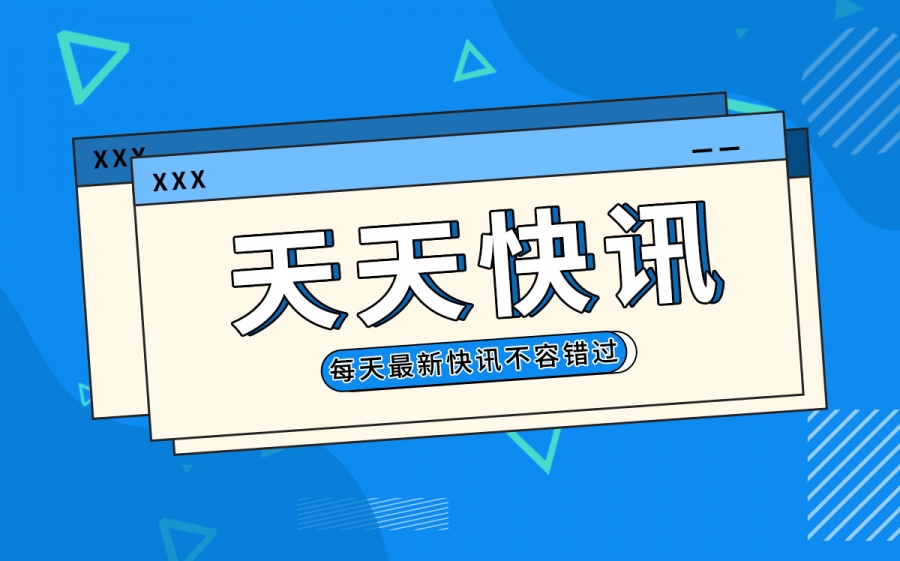
 特斯拉考虑在西班牙建立超级工厂 总规模或达到45亿欧元
特斯拉考虑在西班牙建立超级工厂 总规模或达到45亿欧元 为庆祝保时捷成立75周年 与Xbox合作打造限定主机和手柄遭网友吐槽丑
为庆祝保时捷成立75周年 与Xbox合作打造限定主机和手柄遭网友吐槽丑 大量低价团购票被曝无法进入迪士尼 游客聚集在乐园门口排队等候
大量低价团购票被曝无法进入迪士尼 游客聚集在乐园门口排队等候 紫山药的产地是哪里?紫山药的功效与作用是什么?
紫山药的产地是哪里?紫山药的功效与作用是什么? 寿屋宣布退出《装甲核心6》组装模型 价格等信息暂未公布
寿屋宣布退出《装甲核心6》组装模型 价格等信息暂未公布